《德军占领的卢浮宫》剧情介绍
俄罗斯电影大师亚历山大·索科洛夫自2011年凭借《浮士德》擒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之后就一直在筹备新作《占领下的卢浮宫》。此次索科洛夫将镜头对准巴黎卢浮宫,将时空拽回二战时期,探究纳粹占领下艺术与政治的内核关联。影片已入围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蛰伏四年,俄罗斯电影大师将再度携新作亮相水城,不知能否再夺大奖,但此次作为该片的世界首映,已足够吸引多方关注。 索科洛夫一向热衷于拍摄历史与权力题材电影,其代表作“权利四部曲”中的三部分别涉及:关于希特勒的《莫洛赫》、描写列宁的《遗忘列宁》以及有关日本裕仁天皇的《太阳》。而作为艺术爱好者的索科洛夫对文化收藏宝库的博物馆也是情有独钟,早在其2002的名作《俄罗斯方舟》中就曾取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此次新作《占领下的卢浮宫》更是直接将镜头对准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的法国卢浮宫,定将上演一场有关艺术、政治与文化的历...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斯大林格勒世界再见金陵往事夏之岚春夏冬中穿墙者温暖的印记家庭聚会第三季我,莱昂纳多格莫拉第三季最好的我们大汉风之群雄并起破碎之花集体降职沉默的巡游招摇我和格瓦拉的故事我和她的传奇情仇河岸男孩搜索救援队女仆琳恩医馆笑传2少女☆歌剧RevueStarlightRondoRondoRondo非礼勿闻与神同行:罪与罚大地母亲二次初恋恐怖极限游戏黄金苹果打开我天空腼腆英雄
《德军占领的卢浮宫》长篇影评
1 ) 卢浮宫
一部索科洛夫“玩尽花招”的高逼格违记录神片,突破了电影既定的常规框架,时虚时实的穿梭于过往与现实之间,甚至以一种超现实奇妙的还原手法将历史并入现实,利用丰富的素材和画幅变化,插入许多泛黄老旧的照片和影像追溯历史。
片中有两处极富创意的构思,并未现身的索科洛夫和走入卢浮宫的拿破仑游魂产生的对话和动作牵引,最后打破时空的间隔,直接和当年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交流并告知他们将来的人生走向和结局,让人眼前一亮。
索科洛夫带着讲解、探究和思辨意图的自言自语贯穿全片,对历史做了一个教科书般的实验普及,和见证人民陷入人间地狱的苏维埃俄国东宫的的悲惨命运比起来,逃过一劫的卢浮宫实属庆幸,历史作为前车之鉴,更能体会到自由!
平等!
友爱!
的意义和价值。
2 ) 被击中的日记一则
04/22/16Why was it awe-inspiring? Why was I awe-stiken? It’s the steadiness and coldness of memory, history, nature, altered by power while staying unalterable. It’s Napoléon claiming he went for war for art. It’s the ironic effect generated by the lady beside him repeating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combined with him adding “c’est moi!” It’s the saddening combination (ha, hodgepodge) of art, music, beauty, love, war, famine, cold, death… It’s Jaujard trying to “beg” for life and salvation for his friends from his Nazi “colleague” Metternich, while he’s a civil servant of France who actually works for art, or himself (the art he interprets? Who doesn’t? Who can avoid that?). It’s them two sitting in the chairs, told by us, now, about their future and destiny, when they see the impossibility for them, for all humans, to avoid mundane life and death. And the audience? Audience like me. We felt relieved when we see them fall into worldly cycles, whereas one minute ago, we were struck by the eternity and the holiest statue of art. It’s when you step out, you realize the day is still changing, as is art developing, as is human race charging forward, as are all the stars and planets keeping on spinning. The dusk - the dusk is beautiful - we see couples lingering in the streets, unaware of the changes, the steps.But it’s relieving. I am relieved. I see that I am not the only one - I am but one, if not the slightest one, of the fighters and thinkers of art and life and balance. What’s the meaning? What comes first? What occupies the priority, aka the eternity? There is no answer, even if you are doing it. It’s a trap that no one escapes. There is no chance for anyone to be a great man, who stays in glory in history and eternity. Humans are but humble contributors to art, to beauty, to history; but we ought to feel relived—rather than ashamed or dwelling into escapism—that we are humans, that we make human mistakes, that we are the dumbest of all, in life, in the eternal eye from a place that is no one’s perspective.
3 ) 艺术的破坏
对艺术无感,所以对这个电影也无感,快进看完。
期间,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入侵者的德军会保护卢浮宫?
为什么我中国人自己一直在破坏?
这恐怕是个相当宏大的问题,自忖回答不了。
就这样毫无考证地凭感觉随便说说吧,日后随着知识的丰富和的阅历的增加,也许会持续补充。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我不知道这个古是从何时开始),对艺术并不怎么重视,它属于不入流的技能,它属于“工”,位于士农工商之三,是混口饭吃的奇淫巧技。
家天下集权的政府和提倡的,没人会有兴趣去发展和研究,除非生活所迫。
所以,像阿房宫、北京的城墙、牌楼、故宫里面成堆的画等等,因为仇恨,因为熟视无睹,因为意识形态,就被恣意破坏。
第二,中国对“美”没有感觉,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人一直在温饱线以下挣扎,无法读书,更别提艺术。
当不知道一件东西的美好时,为什么要保护它呢?
北京的城墙,代表的是封建社会,我们新中国要开放,城墙没有存在的必要。
诚然,作为“墙”的功能性,确实没有必要,但它是一件历史文物,承载着文化的意义。
如果城墙必须拆,那么皇宫是不是也应该拆?
它比城墙更加严重地代表封建帝国主义。
那里每天发生着勾心斗角的宫廷内斗,多么腐朽,为什么不拆皇宫?
你们为什么要住进去?
第三,与二类似,不是识字就能保护艺术。
有保护艺术意识的,需要相当高的欣赏水平,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梁思诚提出过要保护文物,还被无情地拒绝了。
4 ) 我们平安渡过了残忍的世纪末
醒醒,安东•巴甫洛维奇,假如您还能醒来的话,请睁开眼睛看看您的剧中人忧郁地眼望着的未来,所有与幸福、与高尚的工作一道如同咒语般念叨着的未来,在一百年后如何变得更加虚弱。
残忍的19世纪末业已过去,而人类居然平安渡过了又一个残忍的世纪末。
契诃夫并未醒来,还有托尔斯泰,叙述者挽歌般的俄语旁白所唤回、所对话的幽灵没有一位属于俄罗斯。
影片自始至终来自作为导演的索科洛夫的俄国人视角(讨论有关这部电影的任何内容时都应切记),而法国是映出了俄罗斯长久的文化焦虑的一面镜子。
谈论巴黎即是谈论圣彼得堡,谈论卢浮宫时,冬宫始终作为一条平行的暗线隐伏于叙事的背面,“这博物馆的价值远超整个法国……谁能想象没有卢浮宫的法国呢?
谁又能想象没有冬宫的俄罗斯呢?
”而谈论上个世纪众多大浩劫的其中一场中不设防的安全孤岛,也即是谈论本世纪。
“什么在眼前等着我们?
”“自由,平等,博爱。
”“我亲爱的玛丽安娜,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自由,平等,博爱,戴红帽子的法国女人如同受到某种启示般出神地说,就像契诃夫晚年那些令人心碎的剧作中的人物所着魔般念叨的某种未来或永远无法抵达、业已消逝的某个处所。
“让我们思索一下,我们死后两三百年,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啊……再过两百年,三百年,抑或是一千年——年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会有一种新的、幸福的生活。
自然,那种生活,我们是享受不到的,然而我们今天也就是为了那种生活才活着,才工作着,才,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才受着痛苦的……”这是契诃夫写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三姊妹》,早于索科洛夫上一部拍摄于博物馆中的电影《俄罗斯方舟》接近整整一百年。
与其表达某种希望,那些不断出现的对未来的想象更像某种剧烈风暴中痛苦的自我催眠,已逝之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或近或远的、业已变得更为苦涩的未来?
与逝者的对话贯穿了整部电影。
在黄色滤镜下的战时巴黎,德军的轰炸机在卢浮宫的低空发出嗡鸣,引发窗棂低沉的共振声响。
一镜之隔的是卢浮宫的肖像画。
那些来自其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目光,他们想对画外的眼睛、对他们自身早已消逝的遥远未来诉说什么?
想想契诃夫、托尔斯泰的遗容,想想他们所无法想象的新世纪,我们死后的世界就像我们出生前的历史一样令人错愕,无论其中哪一个都从未可能对我们开放。
而《德军占领的卢浮宫》是一次搭建对话的尝试,在片中,对话甚至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从俄语叙述者以审判者的身份对Jaujard与Wolff-Mettnich宣读他们的命运,到木乃伊展位玻璃上试图呼唤他们的叩击,这些与历史、与永逝之人的对话始终表现出某种属于俄罗斯的苦涩的幽默感。
“第一次探访卢浮宫时,我震惊于这些脸庞。
正是这些人……这些人,我愿看见的这些人,我能读懂他们,他们属于其各自的时代。
这些法国人,是欧洲历史的人类瑰宝。
我想知道,如若肖像艺术从未出现,欧洲文化风貌将会是怎样?
我若从未窥见前世之人的眼睛,将会成为何许人?
”拿破仑的幽灵出现,他对着镜头外做鬼脸,他指向一幅又一幅肖像画说,“这是我”,“假如不是我,这一切都不可能存在”。
电影中,权力的拥有者始终呈现出某种滑稽的形象,除拿破仑以外,还有被重新配音的影像资料中的希特勒,与在档案照片中和其余从未被叙述者唤回的俄罗斯人一样紧闭双眼的斯大林。
作为一名历史学出身的电影导演,索科洛夫对于权力的探讨由来已久,从1999年的《莫洛赫》到后来的《太阳》与《遗忘列宁》,而在本片中,俄语叙述者对于权力的态度复杂而矛盾,权力使旧世界的文明对于欧洲变得可见,同时令其承受不计其数的损失:无数文物,无数水手的生命,“主啊,主啊,这一切始于何时?
”,丘比特的手指在光线下照得仿佛白蜡一般半透明,人类的躯体必朽,人类的痛苦、尖叫、呻吟永将消散,藉由权力所留下的永远只有冰冷的、没有体温的雕塑,绘画,艺术形式,那么凡人多余的躯壳可作何用?
“博物馆的绘画展厅看起来就像节日游行的队伍,形象地为观众的研究展示了对规定性的过去的一些总体的想象。
在空间上相邻和相连的排列应该使观察者产生一种漫步历史的感觉,使他们能够全景式地俯瞰历史各个时期,并把它们当作统一的历史。
在历史的绘画展厅里时间变成了空间,确切地说,变成了回忆空间,在此空间里记忆被建构、被彰显、被习得。
(Aleida Assmann,1998,p47)”“决定一件艺术品陨灭何处的只有战争”,再次出现时,拿破仑这样对叙述者说道。
“邪恶的国王,邪恶的国家,邪恶的军队,一个欺骗所有人的国家不配存在。
陛下,这不就是您对普鲁士的评价吗?
”普鲁士人在1940年的卢浮宫中游荡,普鲁士人的炮火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将东线所有艺术馆销毁,而叙述者只能苦涩地对拿破仑的幽灵隐瞒普鲁士人何以出现在卢浮宫的原因。
“今天真是糟糕的一天。
我莫名地觉得一切都近在咫尺:风暴,船只,欧洲,巴黎,战争……时间是一个紧紧的绳结。
时间又与它何干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时间与空间上的远方至此汇集在一处,在卢浮宫。
“时间是一个紧紧的绳结”,绳结,这个意象令人几乎直接地感到疼痛,它意味着一切共时在场、密不可分的因果、人物与事件。
在何种时间、何种空间,所有的逝者和逝去的事物会共时出现?
惟有末日的审判,而在此意义上,博物馆亦成了某种审判的象征,那些被权力所左右而遗留或毁灭的所有文明遗存。
从早已不复存在的公元前700年亚述帝国拉玛苏石像的正面,镜头以一种令人压抑的方式缓缓上升,配乐响起了柴可夫斯基Op.39中的一首小曲子,“古老的法国歌谣(Melodie antique francaise)”。
在电影的最后它还将出现一次,当叙述者对片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之一、战时任卢浮宫馆长的、眼神始终充满犹疑与缄默的Jacque Jaujard充当审判者角色念出了他未来的命运。
他将死于1967年,而我们都知道,那个年份处于何种新的风暴之中。
在国内某些版本的钢琴教材中,这首曲子被误译为“古老的法兰西”,像这电影一样,同是被一名俄罗斯人所再阐释的法国,而柴可夫斯基亦被同时代的民族乐派作曲家诟病其过于“法国化”的音乐。
想一想彼得的时代以来整个俄国的贵族如何对法国亦步亦趋吧,而俄罗斯的文化身份,一直以来显示出某种暧昧:来自鞑靼征服者的统治,来自东正教会的洗礼,“既不是纯粹的欧洲人,也不是纯粹的亚洲人”,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这样说。
而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文明中某种宿命性的不幸的根源?
只有当冬宫的命运在叙述中最终出场,幸免于难的卢浮宫与巴黎作为镜像照见被围困的彼得堡、承受兵燹的冬宫,“战争终会结束,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苏维埃俄国”,观众方才意识到,这部挽歌般的电影事实上何其沉痛,尽管俄语叙述者在片中的自我认同是“我们欧洲人”。
将索科洛夫形容为塔可夫斯基的精神继承人是一个未必为他本人所认同的说法,“他喜欢我所做的,但是,实话说吧,我对他的作品颇持保留意见。
从现在的后验视角来看,我会认为,‘我背离他难道不是很有勇气的吗?
’与这位伟大的大师争辩我真是疯狂。
”在2016年的一次访谈中,索科洛夫这样谈及他曾经的老师。
相比全人类,索科洛夫宁可更爱文明本身。
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毕竟在上世纪所有绵延不断的浩劫之后,去爱人类、去为人类的痛苦而承受痛苦显得那么不易,况且人类从来不在乎谁为他们而痛苦。
“我们深深地爱着人类本身,在卢浮宫,一切都是关于人类,人类的挣扎,爱恨,屠杀,忏悔,谎言与哭泣”。
在片头与片尾,海洋作为充满末世感的时间的空间化隐喻出现,一如博物馆是时间的另一种空间化形式,“浩瀚大海上,一浪高过一浪”,满载艺术品的讲英语的文明之船驶离海岸,向着空间的极远处,最终在叙述者所看不见的电脑屏幕上进水,倾覆,我不知道,这艘危船是否隐喻了新的世纪。
5 ) 我们正在驶离海岸
我们正在驶离海岸 “卢浮宫,卢浮宫。
”两个由索科洛夫亲自声演的感叹句,反复传达着人类面对精神方舟式的博物馆时,被唤起的心灵震撼与表达焦虑; 汹涌的大洋上,船长Drik通过网络视频对着导演呼喊,载满艺术品的货轮在与风浪搏斗后被巨浪颓然覆盖; 一群天使跑过卢浮宫清冷的夜晚,玛丽安娜和拿破仑在携手游览,迷醉而讥诮地争吵; 仿手摇式摄影机的画面里,两个历史争议人物找到了微妙的跨国情谊,而真正的史料里,希特勒正通过假想的配音呈现一种俄罗斯式的笨拙…… 如果说13年前与此片遥相呼应的《方舟》是一次人类与艺术毫不停歇的彻夜长谈,那么《占领》则是一场文明和毁灭的默然对饮。
用博物馆投射人类文明,用博物馆的历史境遇去投射人类文明的历史境遇,索科洛夫选择的方式带有一定量的便捷,尽管这种便捷依然徒增厚重。
在当大多数传统历史片还在努力更真实的时候,当代导演们已经开始探讨如何使用不真实的手法使其更有效地真实——而索科洛夫正在做的,是使这种旨向真实的不真实更加不真实——间离一些间离,用一些不确定去诠释另一些不确定,并努力建立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明晰。
几次出场的打板场记员,伪史料画面左侧的声讯波,描述胜利女神像被转移运输,使用的却是现代工人搬运的画面……这一切让观众们在出戏之后进一步被孤立,但并未被边缘化,影像把他们推到一个自省而独立的角度,迫使他们冷静思考。
就连真实的史料镜头也经过了声响处理和戏谑的配音,和还原再现,诗意场景,变形的画作,漫不经心地混在一起,有意降低了真实性。
索科洛夫将所有影像的可信度统一拉到一个模糊的边缘,却未见常规纪录片捉襟见肘时出下策而为的尴尬,反使影片显得统一圆润,并在喋喋不休的旁白里反复升腾。
最后一场戏,是这种非真实被再一次间离的巅峰,两位主角,德国军官沃尔夫-梅特涅(Franz Wolff-Metternich)和和博物馆管理者若雅尔(Jacques Jaujard),先是略显局促地和导演隔窗张望,进而走进屋子,听导演宣判他们未来的人生境遇,脸上挂着惊诧而又无辜的表情,最后他们若有所思地先后走出房间,留下两把空空的椅子——通片庞大浩汤的卢浮宫历史最终归于两个沉默离去的人,这是符合俄罗斯人将冰冷的极简和热忱的繁复相对立统一的独特美学的。
索科洛夫习惯于在影片中扮演自己或自己的代言者,这种习惯使他的作品更加作者。
旁白的身份,有时是经历者,有时是参与者,有时是旁观者,有时是全知全能者,有时则四者皆是。
倘若人们不抛弃日常对话逻辑,任凭它们在灵魂出游中喃喃自语,不和导演就这几者的身份转换达成默契,那就只能迷失在他大段大段俄式旁白构建的语言迷宫里。
让人不禁联想到俄罗斯本国引进电影也从来都是如此操作,一个冰冷的男声,没有角色扮演,没有语气,甚至有时都不肯断句,像个不情愿的朗读者,盖住原声,盖住音乐,与其说是配音引导,反倒更像是一种障碍,但索科洛夫似乎对这种障碍不以为意,他沉醉其中,并使其成为旗帜。
是的,如果你是俄罗斯人,那你就永远都是俄罗斯人。
本片也将《方舟》拍摄地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与卢浮宫两者在二战中截然不同的境遇做了令人痛心的对比,前者虽然经过红军的殊死保护和民兵的抢救,却仍被炮火毁坏大半,并被德军掠夺(作为报复,苏联军队在攻入德国境内后掠夺了德国1500万件艺术品和古董);而后者虽然看上去被法国政府抛弃了(实际上在1939年宣战前,法国就开始有计划地转移藏品),却得以幸存。
这个段落毫不意外得拖沓。
索科洛夫引用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遗容,告诉我们19世纪的终结,父母沉睡,孩童捣蛋,20世纪已轰然奏起。
像Drik的货轮,已经驶离安全厚实的海岸,投身契诃夫描述下残忍的大海,最终被这个沉重的意象吞噬,在Skype艰难刷新的粗糙画质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钢铁铮铮——在卢浮宫里,这个意象被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扮演——影片中的导演却在安全温暖的公寓里,只能看着货轮被大海吞噬,这种隔岸观火的反差和束手无策引发的近乎精神殉难般的使命感,正是索科洛夫回望历史上惨遭劫难的艺术的心情;而“拯救人,还是拯救艺术品”的难题,让影片再一次陷入无解的沉重。
不过,索科洛夫并没有将这种沉重贯穿《占领》始终,纵观全片,反而呈现出一种以往作品里少见的轻快(“权力”系列也有若干,但立刻被覆盖了)。
当德国士兵当街追逐法国姑娘被拒绝,当希特勒闯入巴黎,大喊“卢浮宫在哪儿?
啊!
在那儿!
”当玛丽安娜和拿破仑在卢浮宫里像两个孩子一样撒娇: “自由——平等——博爱——” “是我。
” “自由——平等——博爱——” “没我,这一切都没意义。
” 面对艺术品,前者像凝视爱人,后者像紧盯猎物,共和国的执着和帝国的强势扼要溢于言表。
再比如对亚述人的拉玛苏雕像大篇幅的描述,并企图获悉经由其2700年前传达而来的一种文化对权力的恐惧与反抗。
这是对于“文化与权力”议题的一种契诃夫式的回应,简明而不乏力度。
绕圈,避简就繁,用一种俄罗斯式的冗杂和庞大固埃去对历史进行解构,进而举重若轻地还原和重建,让历史年代隔空对话,并将精神实质抽离,重新编制,迅速揭开伪装,并惊鸿一瞥。
索科洛夫仍旧继续片名里的文字游戏,纵观《莫洛赫》(Moloch1999)、《金牛座》(Taurus2001)、《俄罗斯方舟》(Russian Ark 2002)、《太阳》(The Sun 2005)等等这些过度诗化的名字,他惯于放弃明确直观,转而用一用微妙的方式寻求片名与电影主题的本质联系。
Francofonia直译为“法语圈”,大意指的是世界上所有讲法语的国家们,当人们谈及电影,往往会避开这个生僻冷门的词汇,转而取其副标题,甚至没人去揣测它,但倘若你留意,影片试看和几乎所有版本的预告片都会有这个场景,就是沃尔夫-梅特涅同若雅尔第一次见面的时问到“讲德语吗?
”,若雅尔颓然一笑:“不,我太法国了。
”所以他们在全片仍用法语交流。
这段对话看似无关紧要(但一般出现在影片小样和预告里的,都是导演认为重要的情节),但却对紧扣片名起着关键作用,德国军官讲起了法语,德国士兵在巴黎公园里听起了法语歌,德国人在占领法国后开始为法国的艺术和文物焦虑;这种面对文化不约而同地屈服,和法语圈有着文化深层的共通。
在影像上,此次与索科洛夫合作的仍然是《浮士德》的法国摄影师布鲁诺·德尔邦内尔(Bruno Delbonnel),两人商讨之后,最终选择放弃在《浮士德》《母与子》里大量使用的那些反潜望式的,那些没有透镜只有棱镜的种种稀奇古怪的镜头。
因为使用这些索科洛夫发明的镜头就意味着在拍摄中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调整和尝试,这对于在卢浮宫授权的有限拍摄时间里显然是不可能的。
不过他仍然没有放弃对扭曲画面的偏爱,并将其在后期处理中运用——这种后期的扭曲效果比实拍显得些许僵硬。
索科洛夫1999年拍摄的间离纪录名作《休伯特·罗伯特的幸福生活》里(Hubert Robert. A Fortunate Life 1999,索科洛夫企图用日本能剧来勾联罗伯特的神韵)大量采用自己的特种镜头,造成了一种垂危之人瞳孔放大后看到人生最后一幅场景的效果。
当然曾经担任卢浮宫馆长的休伯特·罗伯特的画作也数次出现在《占领》一片中,其本人也成为影片的一个章节,可见索科洛夫对早年创作的回望。
16年前,16年后,不知他作何感想,再过16年呢?
在2013年,罗西的《罗马环城高速》拿下了属于纪录片的第一座金狮奖,也是在2013年开始盛传索科洛夫要在卢浮宫拍摄另一部《方舟》式的作品,人们开始躁动和期待……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了与预想(甚至和预告片)截然不同的成片。
这是一种纪录片和剧情片的混搭,一种罗德琴科式的拼贴图景。
有媒体说,这次是索科洛夫和众人开了一个玩笑,但索科洛夫应该并不是如此洒脱的人——他严肃,内敛,拥有诗人不具备的开放,和革命者不具备的自我妥协,他的内心尽管矛盾滋生,却怀揣每一个历史学者并不意外拥有的野心勃勃,他甚至坦言自己的绝大部分影片构思(包括在筹备的仍旧发生在圣彼得堡的历史片)是在现今世界上难以实现的。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个人色彩甚至已经抹却了影片的传统分类指标,在这部影片面前讨论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归类是疲乏的,这个影像表达方式和观众接受方式每分每秒都在变幻的时代,使这种讨论更加疲乏。
也许我们还能够在犹豫不定的副标题敲定中推测这次创作历经的患得患失,到底是《德军占领下的卢浮宫》还是《欧洲挽歌》(an elegy for europe)?
前者直接明了,后者让人不禁联想起他惯用的“挽歌”标题(《苏联挽歌》《俄罗斯挽歌》《莫斯科挽歌》《旅程挽歌》……),从这种“挽歌”式的命名中可以推测出一种在索科洛夫的充满悲悯的知识分子复古情结笼罩下截然不同——至少是和我们当前看到的成片非常不同的创作方向。
索科洛夫在影片开头就已经惴惴不安地忏悔——“我想这部电影不太成功,我只是在自说自话而已”。
但也许我们更应该自问,我们企望在一个导演的下一部作品里期许得到什么?
重复还是颠覆?
或更进一步,无我还是非我?
卢浮宫作为制片方之一寄予了索科洛夫极大的支持,毕竟不是每个导演都有机会在自己的影片里触摸丘比特的手指,但由于遭到反对,这部电影还是难以入围戛纳——一向对文化客体容忍度极高的法国会拒绝《占领》,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影片引用的直观影像,比如二战期间法国占领行政划分,德军阅兵巴黎等;而更是由于其语焉不详,态度可疑的政治导向(比如解说词“德国是个复杂而多面的侵略者”),并且这些嫌疑已经在“权力”系列里貌似得到了证实;比如影片里那句长长的反诘——”巴黎有数以百计的博物馆,图书馆,学校,出版社,工匠,民主和习俗,你会为了所谓的原则和政治信仰而抛弃一切,投身一场殃及整个法国包括巴黎在内的大战吗?
” 电影里若雅尔在达芬奇《施洗者圣约翰》前喃喃自问,“为什么要为这样的政府工作”,随后自我回应道“我懂了,我懂了”。
半隐在黑暗中圣约翰,手指上苍,对若雅尔发出诡秘而充满启迪的微笑,这种将历史评判归于不可知论的诠释,大概只会传达给习惯草木皆兵的政客们一种难以启齿的紧张。
直到今天,同一个法国人谈论贝当元帅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图书馆里也很难找维希法国更深层的资料,法国第五频道在今年才首次以纪录片的形式公布了贝当元帅的审判历史影像……面对这种选择性集体失忆,索科洛夫显得勇敢而无辜,正如他自己坦言,“进化像是解构”;在不断的解构中去建造新的视角和解读,焕发传统或使其岌岌可危,这个过程也许伴随着一种令所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着迷的使命感。
兜售身份和兜售立场,寻找身份和寻找立场,还是协同两者去为世界提供一个稳固而崭新的视角,这是导演们在国际上呈现的三种状态或三个章节,有人尝到荤腥,流连在第一章,有些人还攀爬在第二章,索科洛夫无疑进入了第三个章节。
无缘戛纳,也没有俘获金狮,“任性”,“不明觉厉”,“高级”,“目瞪口呆”——但对于已经提前进入后封神时代的索科洛夫,《占领》的确是他诚实却疲乏的非重要作品。
不过他仍知晓自己该如何保持影人立场和作者身份,倘若我们依然把对形式感的一厢情愿框在这位俄罗斯导演身上,恐怕只会被他挣脱地粉碎。
(原文节选载于《看电影》2016年第1期,全文载于公共号“深焦”2016.1.20日推送)
6 ) 《德军占领卢浮宫》影评:“怪异”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关于卢浮宫的电影在艺术和历史中徘徊。
“你好。
那是俄罗斯电影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吗?这里是卢浮宫博物馆。
索库罗夫先生,你不是曾经拍过一部精彩的,用旅行摄影机拍摄的关于冬宫的纪录片吗,《俄罗斯方舟》?我们希望你能来拍一部关于我们的电影。
”我们可以推测,《德军占领卢浮宫》就这样诞生了。
当然,卢浮宫赞助了这个奇怪的档案录像和反复无常的想象。
这部电影与《俄罗斯方舟》的主要区别在于:索科洛夫没有一次在文化巴比伦中漫步,而是在艺术、历史和电影风格的地图上跳来跳去。
他自己在一间昏暗的书房里,用skype与一艘想象中的集装箱船在公海上打滚。
(里面装着艺术珍品。
)接下来,他将对希特勒和被占领的巴黎的新闻片段进行配音。
“去卢浮宫怎么走?”牧师从一辆吉普车上喊道。
最后,也是最持久的——如果不是,你可能会觉得,持久的——我们看到了卢浮宫馆长雅克·约雅德(路易斯·多·德·伦奎赛饰)和德国博物馆领主弗朗茨·沃尔夫·梅特涅伯爵(本杰明·乌策拉斯饰)戏剧性的一幕。
他们共同拯救了宝藏。
他们之间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艺术、文化、国家和命运。
这部电影是一场邪恶的混乱还是一次巧妙的挑衅,随你怎么选。
索科洛夫一直是一位美学冒险家,他在品味、基调和传统的雷区中不断前进。
你可能会对前两个有异议。
影片对野蛮侵略的温和处理似乎是有意无意送给索科洛夫自己的领导人的礼物。
尽管弗拉基米尔正从顿涅茨克赶往阿勒颇,人们不禁想知道他拯救了多少艺术珍品;或者是否有任何善意的电影制作人在Skype与他联系。
By:Nigel Andrews
7 ) 德军的素质
导演选取德军占领卢浮宫的时段,叙事主线讲述卢浮宫及如何在德法两位主角的努力下保存下来;但影片更核心的内容是导演对卢浮宫及文物本身、德法关系以及苏俄二战境遇的个人观点表达!
在他眼中,卢浮宫本身就是欲望和权力的外化,与战争无异;贝当政府的苟全倒戈保全了卢浮宫,但东线的苏俄却遭了秧,于是导演顺便吐了个槽。
导演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呈现历史,本身就试图通过间离手法传达自己的态度……如果本片没有跟上导演的逻辑和表述,容易看迷糊。
8 ) FIFF16丨DAY1《德军占领的卢浮宫》:当艺术与政治交织在一起
第16届#法罗岛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第1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德军占领的卢浮宫》,下面请看前线历史见证人们于其中挣扎的评价了!
果树:跟不上这么高的逼格。
法罗岛帝国皇后:法国人建成它,德国人占领它,俄国人凝视它,窥探历史,成为历史。
Not Here:内容很多,于是这个故事就显得粗糙。
好在功力够深,天马行空却能及时刹住车掌握那个应有的度。
米米:乘载着风浪的“船”, 承载着历史的“卢浮宫”, 承担着自由,平等,博爱的“人”。
艺术最大的价值在于“ta”,安静的“注视着”。
子夜无人:历史的命门就像结尾那两把椅子,执掌生死的操盘手先走了,留下众生去跪求神佛普渡;时代的墓穴就是电影里错综复杂的影像资料、新拍段落、装置艺术品,它们拥挤在一起发生最后的声音,可他其实并无意复原历史、也不想重建时代,他只想植入自我的意志。
Pincent:拼贴式叙述,散文电影,标志性的运动长镜头,出现360度环拍卢浮宫全景,现代的实拍加上仿古的滤镜和演员仿古装扮,再现历史的趣味不少,剧情片与纪录片的边界被打破了,全是导演个人对艺术与政治、战争的私货,比那几部意大利美术馆电影还是高级不少,真正高级的“PPT电影”。
大钊:画面10分,内容8分,价值8分。
没给5星,但是会强推给所有人的一部纪录片。
纪录片不仅需要客观,那些带有主体真挚情感的纪录片常常给人更深的沉浸感。
导演带着对卢浮宫和二战历史人物的复杂情感,引领我们走进历史,被德军占领下的卢浮宫。
包含打板的镜头告诉观众这是场景再现(馆长的表演真是动人),博物馆的作品随着色调的渐进仿佛流转于历史时光,拿破仑是历史人物来到当代与我们的对话,结尾是我们来到历史与过去文明的对话。
空地:1.扭曲画面、特殊色彩滤镜——原“统帅三部曲”的个人所爱(饱含诗意朦胧影像),本片中反倒成了拉伸/缩窄珍贵真实影像资料(1.66:1的画面多次变化为1:1/16:9的画幅)和荒诞/小品化演绎历史现实(有意泛黄、黑绿色以赋予数字高分辨率拍摄画面胶片颗粒感)的电影“罪行”。
2.第一人称在场,伪纪录式调侃观众、戏谑历史人物(敲开历史之门背后的契诃夫、托尔斯泰照片/德法将领+呐喊法兰西“自由平等博爱”的少女),反复中愈加彰显其侵犯性,身为俄国导演(局外人)对个人意识形态/国家民族属性(以史为鉴而宣扬冬宫的艺术保护?
)的强调(投降语言般倾诉表达欲)则显不合时宜。
3.时间沉淀比艺术成就本身更具价值?
一座创作来源不明的雕塑笑而不语。
卢浮宫无需电影的阐释和观众的观看,亲临现场报个中人类瑰宝以凝思才算领略致意。
DAY1的纪录片单元场刊将在稍后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9 ) 散文电影:一种女性化书写
所有伟大的虚构电影都倾向于纪录片,就像所有伟大的纪实文学都倾向于小说。
——让-吕克•戈达尔,1985:181—182一、戈达尔的这句话已经为我们标示出一个悖论:虚构将抵达真实,追求真实将自身瓦解。
我们也许可以举出两部电影来说明这一论点:《阿玛柯德》与《少年时代》。
(扩展阅读:http://movie.douban.com/review/7373465/)这种现象,尤其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后,不断被揭示出来。
新现实主义在影像真实性上所带给我们的有两点:基于理念变革形成的制作新方式,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自由创作等等;同时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电影在还原现实的感知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后者被另一一场运动所标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道格玛95运动”追求手持摄影的真实质感让影像在捕捉现实的能力上迈出了一大步。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当影像不断地“真实化”后,某种自我瓦解便在内部产生。
电影看起来与纪录片越来越接近。
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被欧洲电影人所预见,而是借助几乎发生于同时的伊朗电影人的一系列杰出创作被告示出来。
20世纪90年代的伊朗电影遵循两种模式:一种继续在传统新现实主义旗帜下进行创作,包括马基迪和戈巴迪的儿童电影;另一种则是在前者基础上,将虚构的强力注入影像之中,典型是阿巴斯、莫森•玛克玛尔巴夫和帕纳西的创作,这两股并进的势力一直延续至今。
而阿巴斯在1990年创作的《特写》,不仅在时间上、同样也在创作手法上为这股运动画下了起点。
同样,“乡村三部曲”成为民族影像的杰出典范:伊朗电影人已经从“捕捉真实”上升至“暴露虚假”。
二、以上是从剧情片向纪录片渐进的视角发展出的一条路线,下面我们想将反方向从纪录片入手尝试开辟出另一条路线。
某种程度上,纪录片天然地保证了影像之“真实”,那么从何时开始,“虚构”开始侵入其中。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许需要我们从一场“现代与后现代”的论争中下手。
在七八十年代,法国继结构主义之后卷起了后结构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主将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等悉数放弃了“理性”、“真理”、“进步”等宏大的叙事。
德国哲学家自然也抵御不住这场甚嚣尘上的论争,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规划》中作出回应,称启蒙运动远没有完成,后现代仍未到来。
对此,利奥塔以一本专著《后现代状态》反驳了哈贝马斯的观点。
在利奥塔看来,启蒙运动无非是一种“大叙事”,而在现代社会碎片化的形态下,只有“小叙事”才能相对成立。
这里所言的小叙事指的是一种具有偶发性,受到时间、条件限制,只能部分起作用的叙事。
这种新的观点,导致了客观性和权威效力的瓦解,反映在纪录片制作上,结果自然就是客观性所赖以存在的假设(那个恒定不变的客观视角) 变得不再可信;在现在看来,原先公正与制作真实话语的能力只能被当作一种修辞手段。
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非虚构第一人称电影”的产生。
导演开始尝试在纪录片中加入个人喜好、判断与思考,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发声,通过随机的个人意见来削弱自己的权威。
虽然看起来这无非是另一种修辞,但在一个权威已经消解的世界,这种手法建立了一种诚恳真实的话语,进而尝试与观众进行沟通。
三、拉斯卡罗利将这种新的影像类型命名为“散文电影”,将其看成是对剧情片和纪录片两种分野鲜明的影像类型的融合——“前者是电影人把摄像机作为灵活、透彻、精辟的手段进行个人表达的欲望;后者则是和观众直接沟通,与自我选择的实在的观众建立联系的愿望。
”但在我看来,“散文电影”仍然需要将我在上文所提及的发生在伊朗电影中的情况作下分明。
在伊朗电影中,剧情片仍然是基本形态,只是在其中加进一些虚构成分,可以看成是剧情片向纪录片靠近的举动。
但在散文电影中,保留下来的则是一种纪录片形态,导演在其中加进虚构成分是作为一种对剧情片的模拟来发出个人的声音,更像是纪录片向剧情片靠近。
下面,我们来讲讲散文电影的运作方式。
在拉斯卡罗利看来,散文电影的运作可以概括如下:“我、作者,在反思一个问题,和你、观者分享我的想法。
”她将散文电影分成日记、记事本和自画像电影三大类别,相应的文本承诺如下:“我在记录我亲眼目睹的事件和我亲身经历的印象和情感”(日记);“我记下想法、事件和存在,以备将来之用”(记事本);“我在展示自己”(自画像)。
而索科洛夫的电影被归入第二类,即“记事本电影”。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分析《德军攻占的卢浮宫》的基础。
四、《德军占领的卢浮宫》既然是索科洛夫个人的“记事本”,因而可以写进各种不同类属的主题:历史、政治、艺术……;以及容纳各种不同的影像类型:照片、记录影像、虚构影像……从而成为一个“大杂烩”:将个人所思所感悉数通过影像的方式展示于观众。
如同我们在展开别人的一个记事本之时,通过笔迹、涂改、写下的文字、画下的草图等等,将窥见对方的秘密。
观众作为一个交流对象,也在观影过程中不断“窃进”索科洛夫这位创作者的内心。
这就是散文电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传统纪录片的特质所在:观众并未被看成是一个与作者平起平坐的交流对象,观众召唤而来也不是为了分享作者的经历和思考过程,而是作为一个他者来“偷听”这些自言自语的私人话语。
在《德军攻占领的卢浮宫》中,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位他者,“偷听”到索科洛夫面对德军攻占下的卢浮宫所产生的感受与思考,进而不断从中获取自己的认知和见解。
而电影中的那个画外音,就是创作者尝试与观众建立共谋关系的秘密武器。
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中,索科洛夫的这个声音如同为机器自身所携带,机器生成为一具发声器官。
一方面,它与影像进行双向交流,另一方面它与观众进行单方向的沟通。
前者在《俄罗斯方舟》中已经进行过尝试,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的结尾,这种探索更进了一步。
索科洛夫让诺亚与梅特尼希并排面向观众坐在一起,并向两人告知各自的命运走向,这种奇特的方式已经超越了打破第四堵墙这种低级创意。
后者(与观众建立沟通)在电影中,则是两次对观众的直接发问表现出来——“你清楚吗?
”“你明白了吗?
”,均是创作者与观众单向沟通的尝试。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个画外音,屏幕所代表的摄影机成为连接影像与观众的中介,那个平面(屏幕)成为贯通真实空间(观众观影的空间)和虚假空间(影像所处的空间)的过渡装置。
这当然是一种新的影像制作方式,可以极大拓展影像的展现力。
五、在此,我还想指出,观众对某一类电影形成的误区。
某些时候,彼得•格林纳威的电影被认为与“散文电影”具有某些相似性,但在《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虽然是一部虚构的剧情片,仍然值得探讨)中,作为创作者的彼得•格林纳威无时无刻不在散播强力意志的冲动,与“散文电影”开放的特质有本质区别。
《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中的爱森斯坦无非是他彼得•格林纳威一个人的爱森斯坦,无法生成为任何观众的爱森斯坦。
(这实则是一部集权电影,破解了任何观看的可能性,观众只能被动接受一个“彼得•格林纳威式”的爱森斯坦,没有任何沟通的可能。
)即便彼得•格林纳威与索科洛夫在动用各种影像类型、影像密度上存在某种相似性,但本质的区别在于,“散文电影”从来不会将创作者观点强加于观众,而是通过建立沟通让观众自己去看、去思考;彼得•格林纳威电影中暴露出强烈的男根主义,剥夺了边缘话语发声的可能性。
彼得•格林纳威的电影因而可以看成是“主观电影”,“主观电影”与“散文电影”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仅仅是主观的(甚至是强力的),后者既是主观又是自传式的。
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散文电影”是一种类似女性化书写的影像形态,而另两类影像类型(集权电影与法西斯电影)则是男性书写的典范。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论题,需要建立在大量的研究之上,虽然我相信此点,但我恐怕无力再深入了。
在此抛出这一论题,留给有志之士继续研究。
(注:散文与女性书写的亲密关系,也许可以先从文学史上去寻找,日本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例子。
)扩展阅读:《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49703/) (意)拉斯卡罗利这本书非常有创见地探讨了散文电影的三种形态:日记电影、记事本电影和自画像电影。
但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种类型:书信体电影。
这一类电影虽然不多,但已经被创造出来了,比如《鸿雁传影:维克多•艾里斯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往来影笺》。
10 ) 在博物馆内航行的轰炸机
在博物馆内航行的轰炸机文_唱唱反调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的[德军占领下的卢浮宫]是一部讲艺术的电影,至于它本身是不是艺术,这一点很难说。
于大多数观众而言,这部电影虽然只有90分钟,却完成了艺术的一切——对于以往艺术形式的解构,陈列艺术品的卢浮宫,喃喃自语的艺术家。
但对于索科洛夫而言,这部电影远不能称之为艺术,在他看来,不仅是这部电影,甚至连电影这项发明本身都不配作为艺术的一类。
他认为,艺术这个称谓,应该给更为高雅更为体现悲剧情感的歌剧、绘画、文学,它们远远超越了为民俗文化发声的电影。
这位从苏联时代一路走来的电影大师,为何对艺术有如此罕见的精神洁癖,[德军占领下的卢浮宫]将回答这个问题。
纪录还是剧情 索科洛夫的清高体现在他向来不顾大多数观众的观影感受,影片的开场即是实验的开始。
演职人员表与黑屏分别占据画面的一半,镜头上方的REC开始计时一秒两秒,画外是索科洛夫与一位运输艺术品的船员通话,对方声音与画面时断时续。
接下来索科洛夫试图叫醒沉睡的契科夫,在1904年去世的契科夫,对他死后发生的一切紧闭着双眼,叙述这才开始。
这里的三分钟几乎涵盖了影片所有正在讨论或者说抛给观众去思考的问题。
问题的表征是三种时间的并置与交错。
现实时间是索科洛夫与船员的通话,历史时间是“方才”死去的契科夫同志,影片时间是REC视频录制的时间。
时间的交错表现在,放映时间并非是从零开始,全片90分钟,REC记录的时间是从10:00:00:00开始到11:30:00:00。
REC显得像是某一个时间的截断,像从现实时间中截取下来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在影片时间(通过剪辑虚构的时间概念)一分一秒前进时,历史时间也在进行着。
三种介质的互相交错,恰好与影片在纪实与虚构上的暧昧不清形成了互文。
在人们围绕真实与客观的问题讨论了一个多世纪后,索科洛夫从这些争论中走开,模糊了剧情与纪录之间的差异。
片中有这么一段,索科洛夫讲到德国人入侵法国后,一些法国导演还继续拍片。
画面出现了情景再现与真实历史资料的混合,由演员扮演的摄影师坐在自行车后面扛着摄影机在拍摄,摄影机的镜头被放大,索科洛夫给我们展现了镜头里的画面,它取自当时摄影师拍摄的真实历史资料。
历史资料的在场与摄影师本人的缺席,构成了半真半假的情景再现。
索科洛夫重视的是一种真实感的构建,此时若再搬出纪录片的理论知识,去分辨真实还是虚构已无用处,它给观众直观的感受显然要比学术上的界定更实际有用。
法国导演在危险之下还在进行创作的行为,属于史实,对它的再现严格上来说并不算混淆现实与虚构。
但索科洛夫还在继续挑战严谨的学者。
影片在还原真实的基础上,让历史人物穿梭到现在,将想象的边界进一步延展。
在博物馆拍摄的部分与[俄罗斯方舟]无异,法国重要的人物玛丽·安娜(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和拿破仑·波拿巴(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游魂一般穿梭在卢浮宫。
两位古人的穿越虽然是索科洛夫的假想,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合乎情理,这样的“仿真”真的是“作假”吗?
权力还是艺术 索科洛夫刻意把三个时空差异抹除的做法是一种艺术手法上的含糊,这种暧昧是他对电影技术发展的敏锐直觉所赋予的。
影片中还有一对看起来界限清晰其实却很含糊的概念,权力与艺术。
关于这两者的关系,索洛科夫的态度不再暧昧,他要将这对概念的交叉厘清楚,再把它们分开。
艺术与权力的各自独立,是索洛科夫拍摄这部电影最单纯的愿景,是他想要借助电影这个媒介去反过来作用现实的渴望。
艺术与权力的力量孰更强大?
先来看看卢浮宫内的艺术藏品怎么来的,由演员扮演的拿破仑先是站在《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面前对着玛丽·安娜说:“你看,这里面是我”。
卢浮宫是博物馆,亦是拿破仑的宫殿,这件艺术作品的存在恰好体现了法国权力的意志。
接着拿破仑又指着《蒙娜丽莎的微笑》说:“瞧,这是我的”。
这幅名画出自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之手,它为何会被摆在卢浮宫,虽然史实颇有争议,但索科洛夫却将其认为是拿破仑的掠夺,他把它当成拿破仑的战利品。
拿破仑急于向人们宣告自己对于画作的所有权,艺术在他看来正代表着权力,他是“为艺术而战”的。
在索科洛夫看来,在拿破仑的强权下建造的卢浮宫,与希特勒在二战期间抢夺欧洲列国艺术品,在柏林建造元首博物馆的构想有何不同。
希特勒收藏艺术品,与其说是他的个人爱好,不如说这个做法是借着艺术宣布自己的权力。
因艺术保护者的利益与极权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希特勒承认了卢浮宫生存的权利。
但这却是一个危险的巧合,当艺术利益与政治利益相斥时(斯拉夫文明就被希特勒认为“吞噬普鲁士人纯洁灵魂”的“堕落文明”),艺术则被迫牺牲。
索科洛夫在描述卢浮宫在二战中的“幸免于难”时表达了由衷的羡慕之情,在他的家乡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几乎被被炮火夷为平地。
艺术无力到可以任由意识形态摆布,从生命力来说,它在权力面前的确是孱弱的。
但艺术真的那么孱弱吗?
显然不是,艺术的精神力量远比意识形态要大得多。
索科洛夫用卢浮宫陈列的拉玛苏雕塑轻而易举地回答了这个甚至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创作此雕塑的是亚述帝国(古代西亚奴隶制国家)的匠人,这个带翼的公牛庄严又无邪,它显示出了对权力的恐惧,是恐惧最完美的化身。
亚述帝国早已不存在,但它却保留到现在,包含了人类的挣扎、爱恨、屠杀、忏悔、谎言与哭泣,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永久地传达着世间真理。
冷漠还是深情 从电影技法的角度来说,[德军占领下的卢浮宫]像是沉闷的艺术手法实验台,冰冷无情。
从其中所描述的二战惨状来说,本片也是没有温度的。
它没有对纳粹所犯下的罪恶行径投以燃烧的视线,片中被攻占的巴黎街头并没有战火连天,德军像是在平和的氛围里步入了这位城市,并无多少悲剧气氛,多么冷漠。
它真的是没有情感的吗?
本片的确没有像去年大多数反战题材那般,充当“正确”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但索科洛夫却用了另一种形式传达自己对于战争的焦虑。
在他假想的情景再现中,德国军官弗朗茨·沃尔夫·梅特涅对法国国家博物馆馆长雅克·若雅尔说:“你好像处于永久的焦虑之中,是我的制服碍到你了吗?
”法国是不设防城市,德军的铁蹄步入巴黎时,确实没有激烈的反抗,但纳粹的制服在法国人面前出现,怎可能没有悲剧感。
这种悲剧感如雅克·若雅尔一样潜藏在心中,它上升到了精神层面。
但索科洛夫的深情更多是出于对艺术的狂热,当他将情景再现中的德国纳粹军官梅特涅,与法国国家博物馆馆长雅克·若雅尔(两人合力保护了卢浮宫的艺术藏品)叫至跟前,告诉他们今后的命运时。
梅特涅一直处于阴影中,索科洛夫对他说:“没关系,战后审判时若雅尔会帮你去纳粹化的”。
这句话与其说是告知观众若雅尔之后的命运,不如说是索科洛夫站在艺术的立场,高度赞扬这位跨越了意识形态的鸿沟,敢于同纳粹抢夺艺术珍宝的卫士。
至于那艘载着博物馆的艺术藏品,在海浪中岌岌可危的船只到底沉没了没有,索科洛夫并没有说。
它的最后一次出现是一个大浪打过来,画面已经全黑,那边的声音依稀能听见,索科洛夫大声对船员喊道:“快把货物扔掉,不然你会没命的”。
但船员却并不愿意放弃,甘愿为之付出生命。
这是索科洛夫想要表达的理想主义式的深情,是现今人类对艺术葆有的最美好的情结,也正是本片跨越了所谓的历史、道德与政治想要传达给观众的。
刊于《看电影》周刊 2016年1月 未经允许 请勿转载
个人公众号:电影少女放浪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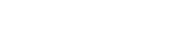

























说教、幼稚、苍白。糟糕的摄影和完全自我陶醉的后期处理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位在集权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作者,血管里绝没有半滴昂格鲁撒克逊人的血液。看见“美”时,除了高呼“美哉!”,我们亲爱的导演就没有别的任何反应了。调色真的糟糕,自制的仿古风格的录像也太假太出戏。要不是等会儿还要看个话剧想借影院睡个觉,我现在一定离开了。
感觉 片里所有对白的潜台词就是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一看他鬼扯拉玛苏是什么权力恐惧,就嗅到了知识分子的腐烂臭气。别怪人说ppt,这他妈连ppt都不如,写论文你就好好写,揉进去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杂碎,论文本身的史料也粗糙且表面化,所以我给不及格。知识分子就这点不好,非要把所有东西都按自己的来,明着高喊反对独裁,实则自己就意识形态的不得了
挺无聊的
上海电影节首次接触,验证了自己之前的预测,完全看不懂,没想到一句玩笑竟然成真。。再来看评论,居然能有人写出这么多字的评论,感觉好惭愧,我是真的不文艺。
三星半//这样将宫殿化用作博物馆展示各个时代的精粹很难不想到《俄罗斯方舟》啊 但这里的展现形式更多元 纪录影像与套层结构与搬演//然而似乎这一切还都不够有趣 或者说是多元的形式冲淡了内容可能呈现的有趣//艺术很难做到字面意义上的纯粹 只能在一定程度表现纯粹 这很讨厌 说明了艺术在某种角度的空洞//嗐要是这样想就真的徒增忧愁了
浩瀚海洋上,一浪高过一浪,他们残酷无情,也无悲悯
仿佛将卢浮宫的内涵通过电影展示给了观众,但其实是很好的给观众催眠了。
大人文关怀主义。一些镜头设计匪夷所思,得见导演一丝作者之魂在历史长河中恣肆徜徉。
这种形式的对话 有点灵魂追问 身临其境的意思
"Who needs France without the Louvre? Or Russia without the Hermitage?"
四大才去了一个,啥时候第二个?这个比方舟好看点。
20200704 是个散文电影,通过二战德军占领卢浮宫的视角,回顾卢浮宫的历史,最后结尾不理解...
看不进去……元首还是很帅哒……
纪录片+电影
高阶的纪录片,但还是乏味
历史是一缕游魂,飘荡在卢浮宫内。而时间就是它的囚徒,岁月凝驻美即永恒。拿破仑与玛丽安娜静坐无言凝视着蒙娜丽莎,沃尔夫·梅特涅和贾克乔札面面相觑听从未来预言。移转的巴黎远景仿佛也将时空搬离,导演的私人化解说似洪钟大吕回荡在历史的回廊中,佶屈聱牙。硝烟中的艺术无可奈何,只好听天发落。
2016.4.13
要不是为看看卢浮宫啥样,要不是为看看那些二战老片段,我特么才不捧什么特么大师的场呢!困的我....
神乎其技的各种穿越对接,稍带上俄罗斯人的酸意: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整个欧洲都是一家人,其实人家西欧各国互相当对方是嫡亲,把东边的都看作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