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举证》剧情介绍
泰莎(朱迪·科默 Jodie Comer 饰)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刑辩律师,热爱胜利。她从工人阶级出身一步步成长为顶尖律师,在任何案件中都能进行辩护、交叉质证和消除疑点。她不对客户做价值判断,不相信一面之词,甚至不能相信自己的直觉,她只相信“法律下的真相”,法律与系统会做出最接近真相的判决。但一个意外事件迫使她直面父权制下的法律、举证责任和道德之间的分歧。 在2023英国劳伦斯·奥利弗奖评选中,该戏剧获得最佳新剧奖,朱迪·科默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心灵想要大声呼喊不可告人生而抱歉惊奇队长2牢笼小鼠和大象的创意1883商道绑架2沒有水的大海读或死陪审团十二人第二季人事美魔女·椿真子意学研究一号档案守护者反复无常翻译风波兴风作浪护理师国民老公2热巴情尤利西斯:贞德与炼金的骑士越野飞车嫌疑人第一季别叫我酒神2陀枪师姐2纽扣战争他来了,请闭眼雷霆悍匪游戏
《初步举证》长篇影评
1 ) 《Prima Facie》Bravo! Bravo!
昨天被B站推送了National Theatre Live的新话剧《Prima Facie》,因为撇了一眼是律政题材,我就下意识点开视频,结果几乎是一口气看完,期间落泪数次,情绪也久久不能平复。
该剧的梗概,就是一位出身平凡的英国女生,通过不懈努力考入剑桥学习法律。
毕业之后,她成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屡屡凭借巧言善辩,帮助被告人打赢官司。
眼看未来一片大好前程时,她却在某天晚上被约会的男同事酒后强暴,从此开始了人生噩梦。
在经受了782天的身心折磨之后,她以原告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只为将伤害她的人绳之以法。
简单说几点我的观影感受吧:1、Jodie Comer的全场表现,值得落幕时观众们的standing ovation,我想她的演艺之路一定会前途无限。
虽然至今我也没看过《Killing Eve》那部大火的美剧,但Jodie的话剧首秀还是让我真切感受到,她一个人在台上撑起近2小时的戏,得需要多大的体力和才华呀。
Jodie不仅酣畅淋漓地呈现大段大段的台词,还能借助肢体和音色变化,再现不同人物的戏剧冲突。
同时,她还不断更换装束、移动道具,以便快速切换剧中场景。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Jodie表演的某些瞬间,会联想到另一位英伦才女演员Emma Thompson的模样和声线,总之是对她一见如故,大为欣赏。
2、最近十来年,英国的文艺创作者在女性议题的讨论上,确实做到了不断突破和深化。
我记得,在2011年BBC推出的律政剧《Silk》中,有一集就是关于某女性被前男友性侵的案件。
剧中的辩护律师Martha(也是我最爱的英剧女主角)极不情愿接手此案,为可能有罪的男方辩护,因为她深知:每一位声称遭受性侵的女性,都会被警察和律师无情盘问:她们是否穿着暴露、是否喝酒过量、是否生性放荡、是否投怀送抱。
最终,性侵案件的定罪率是极低的,在社会影响上也会对女性权利的争取愈加不利。
然而,出于律师的职责要求,她不得不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客户洗清罪名,目睹未能胜诉的女方在法庭外情绪崩溃。
在本集的最后一幕,Martha回到家中,伴随着唱片机里的悲伤灵歌,独自一人默默痛哭。
如今2022年,类似的题材再次被搬上舞台,最后的结局还是一样令人失望。
但是,这次的女主角Tessa,因为既有过像Martha一样为潜在性侵施暴者辩护的经历,又有过身为性侵受害者无力举证的不幸遭遇,她最终勇敢地在法庭上指出:现有的法律体系,总是要求受害者的证词逻辑清晰,只有这样它才能被当作可信的定罪依据。
当女性受害者面对律师咄咄逼人的诘问,出现情绪波动、言词不一时,就会被认为是当庭说谎、进而输掉整个官司。
可现实是,女性对性侵过程的细节记忆,很可能是混乱不清的,因为她们在案发那刻,经受着极度的身体恐惧和精神创伤,也因为她们在日后,面对种种质问和异样眼光时曾产生过自我怀疑。
所以,性侵案件难以定罪的问题不在于女性,而在于法律本身。
人类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法律框架,是一代代男性主导制定的,它没法从女性角度来展现全部真相,实现公平正义。
或许,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事情,是去质疑和改变现有法律,而不是漠视或拷问每位受害者。
最后,还是记录下《Prima Facie》剧中的一段原话,希望能引发更多人去思考社会现状,发出微弱却宝贵的声音;也希望国内的影视编剧们,能跳出“霸道总裁爱上我”、“后宫佳丽争君宠”的老套题材,不断向高手学习,精进业务水平呀。
“There was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courts like this did not see non-consensual sex in marriage as rape, did not see that battered women fight back in a manner distinct from the way that men fight. Yet once we see, we cannot unsee, can we? Now I see, from my own experience, that we have got it all wrong when it comes to sexual assault... The law is an organic thing. It is defined by us. It is constructed by us, in light of our experiences, all of ours, so that there are no excuses any more. It must change because the truth is that one in three women are sexually assaulted, and their voices, they need to be heard, they need to be believed, in order for justice to be done.”
2 ) 不要杀死自己的内在小孩
初步举证 (2022)9.52022 / 英国 / 剧情 / 贾斯汀·马丁 / 朱迪·科默这部电影的后劲太大了,以至于我看完电影吃饭的时候,还几度哽咽,觉得难受。
电影讲的是关于正义、侵犯和司法体系的大问题,但里面有几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1、泰莎在报警后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觉得连累身边的家人、朋友、同学和同事,在之后的782天里,没有回应前同事“可以找我帮忙”的善意,因为觉得羞愧,开庭时也只有妈妈出现,而且妈妈非常坚强,没有作出任何表情来影响泰莎。
反观朱利安,不仅请各路人士给他写信证明“清白”,还有同学到现场“助威”。
2、泰莎有过纠结,要不要报警,但是最后促使她报警的,是她害怕如果不这么做会伤害自己的内在小孩,让自己不再是自己。
这个叙事简直太熟悉了,女孩们需要做多少事、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让自己信任自己,向自己证明自己,面对被侵犯这种事,真的也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杀死自己的内在小孩。
3、泰莎和朱利安在办公室睡了,女孩和朋友们说的是他很可爱,想进一步发展,朱利安却是到处炫耀,甚至在下一次女孩精心准备的约会当晚qiangjian了她。
女孩们也想强调xing解放,但是这个社会环境里,越是解放,受伤更深的不越是女孩吗?
但我觉得泰莎会走出来的,因为她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更多人。
卷宗一卷一卷亮起的那一刻,我明白我们都会帮助自己的。
3 ) 她举重若轻的演技让我惊叹
太牛了,凭借一个人的力量让很多画面生动地浮现在人们眼前。
我简直太震撼了。
而且我也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跟吃了一只青蛙一样哑巴了叫不出来的感觉。
自愿和非自愿仅仅只是一线之隔,在时间上甚至是一瞬之隔,在语言上可能可以轻松地迈过,在法律上却隔了一座大山。
女性有口难言,说不清楚。
男的则都觉得无所谓,矫情。
婚姻和恋爱关系成为了很多恶行的遮羞布,好像在这样的框架内,很多恶劣的行径突然无足轻重。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呐喊呢?
我又想起我发布了男的总是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帖子时,本来只是想抒发我交朋友的边界感总是被打破,被暧昧化,被两性关系化。
却收获了不仅来自男性而且来自女性的攻击。
“你们没有任何特权”“你如果生理性厌男就不要浪费他们的时间”“你真的很奇怪,看不出来他们喜欢你吗”原来男性的任何行为被冠以“喜欢”,就可以被轻飘飘地合理化。
这和小时候“喜欢你”的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你,又有什么区别?
这个世界究竟要替男性遮多少羞。
我对亲密关系没有任何愿景,看到有愿景的男性也知道他们只是想找一个保姆、一个发泄性欲的对象、一个自甘受辱的人、一个可以捆绑一辈子的称号。
世界上的蠢货那么多,我只希望女性中这样的人可以少一点。
不要再冷漠地站在自己同胞的对面,看不出来男性过得已经有多好吗?
他们的时间根本不需要我浪费,他们自己冠冕堂皇地浪费了我很多时间。
同样,我也脱下了对于男性的学识滤镜,虽然不是totally,但也快了。
这还是多亏了我学的专业。
他们的学识看起来再怎么渊博,本质上还是服务于自己的特权,为了维护父权的利益,不可能用于帮助我、建设我。
学识只是学识,看是谁用,一个冷冰冰地只会引经据典的没有人性的机器,即使能够纯熟地运用各种知识,又与我何干?
又算得上有什么魅力呢?
我永远不可能受益于他们的学识。
书看得越多,越自以为是,越高高在上,越冷漠,越要调转矛头指向我们,越看不起人,越趋近于男性的本性,越像退化的人类。
4 ) 我不是为了赢而打这一场仗,而是因为这场仗必须打。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新的年度佳作。
第一次在电影院看戏剧官摄就遇到了这么好的作品真是幸福啊!
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这些事情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能假装没有发生,有些事情必须改变!
曾经的泰沙笃定地相信这法律体系,可这一切在她的身份对调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她坐在那个小房间的时候,她才体会到,詹娜有多么孤独。
当你被伤害,被审判的却是受害者,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那些痛苦的经历,这样的法律,是有缺陷的,必须改变!
我知道,他们会给出怎样的判决,但是就像詹娜一样,这一切并非徒劳无功,我们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罪行的审判,都能撼动看似坚固无比的这栋老古董房子一点点。
这很艰难,但有意义。
因为,我们打仗不是为了赢,而是因为这场仗必须打。
5 ) 再看初步举证 注意到好多母女线的小细节
这是第二次看初步举证了,第一次还是窝在宿舍小小的床上,盯着电脑屏幕认真地看下来,这次在大屏幕上看更为震撼,也发现了很多第一次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这次似乎更能发现泰萨和妈妈之间的爱了,父亲去世,一个单身母亲独自养育着三个儿女,承担着生活的琐碎和压力,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会情绪不好的向女儿泼冷水,会对儿子们有偏爱,但是不可否认,她一定也很爱她的女儿。
在如此艰难的经济状况下,她能够支持女儿读完剑桥大学法学院并支持她成为一名律师;为女儿买下的那件材质廉价的粉色衬衫,或许是她能买到的最像样的衣服;在女儿遭遇痛苦的时刻,她能接纳她所有的眼泪,并抱住她;在女儿因为施暴者而难回职场感到沮丧时,坚定地对她说,打起精神来!
你不能因为这件事这个烂人,毁了你的前途和你这么久的努力!
每当泰萨拿起那件粉色衬衫,她捧着它深呼吸,都能感觉到她似乎从那件衣服上感受到了妈妈的味道,获得了前进的勇气。
在法庭上,妈妈冷静克制,双手紧握着那个沙滩包,她内心一定比女儿更痛苦更难过,但她作为女儿的后盾和力量,容不得自己一丝懈怠,于是她坚强地坐在听众席上,最后走向女儿,带她离开法庭。
写到这里,眼泪就不自觉的流下来了…或许是因为现在上班了的缘故,我更能看到这对母女之间的感情了,自从上班之后我妈妈也总是爱为我添置各种职业装,于是总会不自觉的代入进去(笑)偏个题,我真的好爱妈妈啊🥰最后,最近容祖儿很火的没关系这首歌和泰萨好配🥹亲爱的,坚强地、大步地向前走吧!
败诉也没关系,最后亮起的那面档案墙会照亮所有人前行的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迎来想要的结果🥹
6 ) 当一个女律师遭到性侵
今晚在电影资料馆看了《初步举证》放映。
上一次看独角戏放映还是《伦敦生活》,果然真正有张力的戏剧只需要一个小剧场和一个有极强舞台表现力的优秀演员。
一个经常接手性侵案件、从无败绩的一流辩护律师、外人以及自认为的女强人,在遭遇了性侵后,如何打碎自己的认知并且重塑对法律、对生活的信心?
泰莎坚守自己多年习得的法律知识和从业习惯,并不能让她成为法庭上胜利的原告,也不能让她的精神更好过。
为什么,站在法庭上无数次要重述侵犯过程、面对交互询问的是受害者?
当受害者不是“完美的”,她就成为不可信的证人?
如果她曾经与被告有过暧昧关系、她着装举止不够端庄,是否就是“仙人跳”?
正如现实中刘强东案件,当初多少人看到被告对刘微笑和礼貌,就认定是一场“没谈好价钱的性交易”,其中包括很多女性。
曾经质疑性侵案受害者的泰莎自己亲历了一切,才醒悟由男人主导制定的法律是错误的,在这样的法律系统里根本得不到公平与正义。
就连平日如此冷静、强大的女性,也会“愚蠢”地在事后马上洗澡毁坏证据,会怀疑自己是否小题大做,会面对强奸犯时颤抖恶心想要逃避,更何况许许多多普通的女性。
如果不能让受害者得到安全感,就不会有更多受害者站出来,当然也更不会有更多的正义。
在剑桥法学院时坚持苦读的岁月、在看到法庭上那个穿着不合身制服的年轻女警员时,让泰莎勇敢地,在几乎全是男性的注视下,喊出了“我们需要改变。
”第一次看朱迪科默的戏还是《福斯特医生》里破坏女主婚姻的任性白富美,然后就是《杀死伊芙》的小变态。
这位年轻的女演员对舞台的掌控力和爆发力比在影视剧里更加惊人,看完后如同被一记重拳痛击,久久震惊。
前期她是意气风发、前途一片大好的律师,当她独自一个人重现被侵犯到站在法庭上举证的过程,她的颤抖、喘息、哽咽、落泪、愤怒……丝丝入扣,完全就是一个在经历反复羞辱和折磨后依然站起来的泰莎。
最后穿的那件妈妈给的粉色衬衫,让我想起《律政俏佳人》,在充满代表男性的黑色洪流里,她们独自逆行而上。
7 ) 性侵证言的“可信度打折”
非常震撼的独角话剧,从观念内核到剧本写作到表演功力到舞台设计都是毫无疑问的满分。
剧中揭露的法律设计上的根本缺陷,我在《“我也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运动》(收入《空谈》第52-113页)一文中专门做了分析,这里姑且摘录相关章节代作影评吧。
空谈8.9林垚 / 2024 / 上海译文出版社第94-95页:『对性侵扰遭遇的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也会进一步造成对受害证言的不合理挑剔。
比如指控者“无法想起某些关键的时间地点”或者“在数次口供中对部分受害情节的描述前后不一”的情况,常常被认为足以证明其指控的不可靠。
然而相关研究早已表明,人类在遭遇严重心理冲击的情况下,的确经常只能对详细的事件过程形成较为碎片化的记忆,并且遗忘时间地点等“抽象”元素,却对周边的声音、气味等“感官”元素留下鲜明持久的印象——性侵扰受害者在这方面并不例外[15]。
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无知或无感,加上前述的性别偏见,便使得性侵扰案件的实际判断结果大幅偏向假阴性一侧……』(前文从略)§4.1 虚假的性侵扰指控比例究竟有多高?
在各类性侵扰指控中,“虚假(false)指控”的比例究竟有多高?
这是犯罪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公检部门在罪名定义、证据标准、办案方式、统计口径、数据完备性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不同研究者在数据使用方法上的分歧,均令相关研究长期无法达成一致结论。
2006年的一份综述罗列了1974至2005年间发表的20份论文或报告,其各自推算出的虚假强奸指控率,跨度竟然从1.5%直到90%,可谓天壤之别[1]。
不过更晚近的研究在方法上有所改进,结论跨度也大为缩小,基本上处于个位数百分比区间。
比如:2009年对欧洲九国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些国家执法部门官方判定的虚假强奸指控比例从1%到9%不等[2];一篇2010年的论文分析了波士顿某大学1998至2007年间138件校园性侵指控的卷宗,发现其中有8件(5.9%)被校方判定为虚假指控,而这8件里有3件(2.3%)的指控者承认确系谎报[3];发表于2014年的一篇论文,基于2008年洛杉矶警察局的性侵报案记录以及对办案警员的访谈,推测其中虚假指控的比例大约为4.5%[4];2017年的一项研究通过整理2006至2010年间全美各地执法机构的办案结论,统计得出这段时间内强奸报案“不成立(unfounded)”的比例约为5%(“不成立”报案的范围大于“虚假”报案,还包括其它情节较轻达不到执法标准的报案),低于抢劫(robbery)报案不成立的比例(约6%),但高于谋杀(murder,约3%)、殴伤(assault,约1%)、入室盗窃(burglary,约1%)等其它类型报案不成立的比例[5]。
虽然近年的上述研究结论逐渐趋同,但它们对虚假指控比例的计算均基于执法部门本身的案卷归类,无法完全排除后者统计口径不合理或办案偏见方面的影响,因此仍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比如英国内政部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尽管英国警方将强奸报案的8%登记成“虚假指控”,但其中大部分卷宗明显未能遵守内政部的办案指南;在看起来遵守了办案指南的卷宗里,登记成“虚假指控”的比例便已降到3%;而且无论是8%还是3%,都远远低于办案警员在访谈中对虚假指控率的猜测(比如有警员声称:“我过去几年一共经手了几百桩强奸案,其中我相信是真实指控的,大概只用两个手就能数得过来”)[6]。
其它国家关于执法人员偏见的定性研究也得出了极其类似的结论,比如在2008年发表的一项对891名美国警察的访谈中,竟有10%的警察声称,报案强奸的女性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在撒谎;此外还有53%的警察断言,这些女性里头有11%到50%是在撒谎[7]。
警员对性侵扰报案者(尤其报案女性)的严重偏见与敌意,一方面意味着,即便在遵守了办案指南的卷宗里,也可能仍然存在大量被错误定性为“虚假指控”的案例。
这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新西兰的连环强奸犯马尔科姆·雷瓦(Malcolm Rewa)一案:早在他第一次犯罪时,受害者便向警方报案,并提供了抓捕雷瓦的重要线索;但新西兰警方出于对性侵受害女性证词的高度不信任,在对受害者进行了一番程序上的敷衍之后,将其报案登记为“虚假指控”束之高阁,导致雷瓦长期逍遥法外,又强奸了至少26名女性之后才最终落网[8]。
另一方面,执法人员的偏见与敌意也意味着,有大量的性侵扰受害者因此放弃报案,间接抬高了卷面上的虚假指控率。
比如英国政府平等办公室2010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英国小区组织“强奸危机中心(Rape Crisis Centers)”的员工与警方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只有19%的员工表示,自己在被熟人强奸后会向警方报案[9]。
英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发布的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年度犯罪调查报告同样发现:在遭到性侵的女性中,只有17%选择了向警方报案[10]。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在统计虚假性侵扰指控比例时,更有效地排除执法人员偏见导致卷宗错误定性对资料的干扰?
英国皇家检控署在2013年的报告中独辟蹊径,通过对比检方起诉性侵扰嫌疑人与(以“妨害司法罪”或“浪费警力罪”为由)起诉虚假性侵扰指控嫌疑人的数量,来判断虚假指控的比例;毕竟如果办案警员不是基于偏见胡乱登记“虚假指控”结案了事,而是一视同仁地严肃对待真实指控与虚假指控,就会把虚假指控者一并移交检方起诉。
该报告指出,从2011年1月到2012年5月的17个月间,英国检方一共起诉了5651起性侵扰案、35起虚假性侵扰指控案、3起虚假性侵扰指控兼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11]。
换句话说,根据英国警检部门的实际行为来判断,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比例仅为0.67%(5689起中的38起),远远低于前述所有研究的结论(并且这还尚未校准因为大量性侵受害者一开始便放弃报案而造成警方卷面上的虚假指控率虚高)。
毋庸赘言,检方对指控真实性的判断并不总是准确(注意这种不准确性是双向的,既可能错误起诉某些遭到虚假指控的嫌疑人,也可能错误起诉某些做出真实指控的受害者);而刑事庭审虽然采取极其严苛的“排除合理怀疑”等标准、并因此基于残留疑点而放走一部分真凶[12],却也仍旧无法完全躲避误信虚假指控、做出错误定罪的风险。
不过这些错误定罪的案件,大多数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于一般人对“虚假指控”的“报案者根本没有遭到任何性侵扰、所谓受害经历纯属瞎编”式想象。
比如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全美冤狱平反记录中心(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截至2016年底录得的、全美289起嫌疑人被法院错判有罪的性侵案件中,71%(204起)是陌生人性侵,尽管陌生人性侵只占全部性侵案件的大约五分之一。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错判有罪的性侵案件中,绝大多数(228起,占全部错判的79%)都是因为警方及检方搞错了作案者的身份,而这又基本上(200起,在搞错身份的案例中占88%)是因为受害者或其它目击者无法在一群陌生人中准确辨认出作案者(熟人性侵案中也有搞错作案者身份的情况,往往是因为受害人出于种种原因不敢或不愿指证真正的作案者,导致对警方和检方的误导)。
美国“黑人男性性侵白人女性”类案件的虚假指控率与错判率之所以高得出奇,除了白人社会及司法系统的种族偏见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类天生在“跨种族面部识别”方面能力不足,导致白人受害者及目击者经常误将无辜的陌生黑人当成实际作案者[13]。
综上所述,其一,现实中性侵扰报案的虚假指控比例本就很低,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要么与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报案比例处于同一量级(个位数百分比区间),要么其实是再往下一个量级(个位数千分比区间);其二,社会文化及执法系统对性侵扰受害者(尤其受害女性)的偏见与敌意,又令现实中绝大多数性侵扰事件未被报案,间接抬高了官方资料中的虚假指控率。
对比可知,MeToo运动“催生大量虚假指控”的可能性,被质疑者不成比例地高估了。
其三,在导致冤狱的虚假性侵指控中,绝大多数确属真实发生的陌生人性侵,只是搞错了陌生作案者的身份。
与此相反,MeToo运动曝光的均为熟人性侵(毕竟若不知道对方身份,曝光便无从谈起),所以对冤狱概率的估算还可以进一步下调。
§4.2 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男子气概、“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当然,诚如MeToo质疑者所言,无论概率多低,虚假指控的可能性永远存在,因此理论上说,MeToo运动的展开、性侵扰证言的受到鼓舞,必然会令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至于比例则可能增加也可能下降);换言之,理论上一定会有某个无辜者因为MeToo运动而遭到虚假指控、甚至错误定罪。
对此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1)首先需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不管什么类型的案件,在给定的举证责任标准下,报案数量的增加,理论上都意味着虚假指控与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随之增加,反之亦然;同样,给定审理案件的数量,对举证责任标准的任何调低,或者对指控方置信度的任何调高,理论上都意味着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以及比例)随之增加,反之亦然。
同时,就算在刑事案件中严格遵守无罪推定原则、严格要求控方“排除合理怀疑”,由于断事者身为并无“全知”能力的人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判断上的失误,冤假错案仍旧会时不时发生。
要想完全消灭冤假错案,唯有拒绝接受任何报案,拒绝在庭审中相信任何不利于辩方的证据,或者拒绝做出任何有罪判决。
这显然不是可行的办法。
尽管以剥夺基本权利为手段的刑事惩罚的严重性,是我们在刑事判决的假阳性(冤枉好人)与假阴性(放过坏人)之间权衡取舍的重要考虑, 但我们不可能为了百分之百消灭某种性质极其严重的假阳性结果(比如有人被错误地剥夺基本权利)而让假阴性结果超出某个可以容忍的限度。
所以真正的问题永远是,如何判断假阴性结果的恰当限度、如何在假阳性结果与假阴性结果之间找到最合理的平衡。
(1a)前文已经提到,在举证责任层面,这种平衡体现为“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优势”等不同证据标准之间的选择。
但在有了相关证据之后,怎样的怀疑算是“合理”怀疑?
双方证据究竟谁占“优势”?
这就涉及到证据评估层面的具体判断。
而人们对证据可信度的判断,总是受到或内在于人类认知机制、或从社会文化习得的种种偏见的影响;有了适当的举证责任标准之后,总体结果能否尽可能地向假阳性与假阴性之间的最合理平衡靠拢,便取决于证据评估过程中能否尽可能地剔除系统性偏见的影响。
父权社会普遍而系统的性别偏见,无疑是影响人们对性侵扰指控可信度判断的最大因素之一。
正如前引的诸多调查报告所示,受理性侵扰案件的警员,总是极其严重地高估虚假指控(尤其是来自女性报案者的虚假指控)的比例。
对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credibility discount)”现象由来已久,而且普遍存在于性侵扰指控之外的其它各种领域[14]。
这种不信任,一方面出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理性能力的贬低(认为其与儿童一样“理性尚未发育完备”),另一方面出于父权社会对女性(在某些问题上或某些情况下)的道德猜忌:比如所谓“最毒妇人心”,亦即认为女性的道德下限低于男性;或者“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亦即认为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以及有过较多性伴侣或性经验、因此被指“私生活不检点”的女性)绝不可信。
面对性侵扰指控时,这些偏见既导致对指控者意图的高度怀疑(“我看当时其实是你情我愿半推半就,只不过办完事儿后悔了想假扮纯洁?
或者根本就是闹矛盾了故意陷害对方吧?
”),又导致对受害证据(尤其是证言)的无端挑剔。
(1b)对性侵扰遭遇的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也会进一步造成对受害证言的不合理挑剔。
比如指控者“无法想起某些关键的时间地点”或者“在数次口供中对部分受害情节的描述前后不一”的情况,常常被认为足以证明其指控的不可靠。
然而相关研究早已表明,人类在遭遇严重心理冲击的情况下,的确经常只能对详细的事件过程形成较为碎片化的记忆,并且遗忘时间地点等“抽象”元素,却对周边的声音、气味等“感官”元素留下鲜明持久的印象——性侵扰受害者在这方面并不例外[15]。
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无知或无感,加上前述的性别偏见,便使得性侵扰案件的实际判断结果大幅偏向假阴性一侧;所以若要达到假阳性与假阴性的恰当平衡,相应的矫正无疑是,争取调高人们对性侵扰指控及相关证据的“缺省置信度(default credence)”。
(2)性别偏见的影响,还不仅仅体现在性侵扰指控的证据评估层面,而是一开始就型塑了人们看待“虚假指控”问题(及其严重性)的视角。
比如前面提到,即便采用“个位数百分比区间”的估算结果,强奸报案不成立的比例在各类刑事案件中也并不高得出奇,甚至还低于抢劫报案不成立的比例;但绝大多数人在对虚假强奸(或其它性侵扰)指控忧心忡忡的同时,却并没有对虚假抢劫指控的“泛滥”抱有同等程度的恐慌与敌意(甚至绝大多数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虚假抢劫指控的问题,更不用说对其有任何恐慌了)。
产生这种差异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由于父权社会的潜移默化,人们在抽象地思考案件时,很容易自动代入男性中心视角。
由于性侵扰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女性、作案者绝大多数是男性、指控绝大多数时候是女性针对男性做出[16],因此男性中心视角很自然地导致对性侵扰指控的过度焦虑与怀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是虚假指控该怎么办?
“他”的人生不就被“她”给毁了吗?
相反,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指控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尽管某些阶层(比如穷人、流浪汉、进城农民工)或族群(比如美国的黑人)可能特别容易遭到虚假指控,但这些阶层与种族往往在话语权方面同样处于劣势,他们的视角因此更容易被主流社会文化忽略、而不是得到代入。
(2a)需要注意的是,旁观者此处自动代入的“男性中心视角”,严格来说其实是一种“滤镜后的(filtered)男性中心”视角。
尽管从比例上说,绝大多数性侵扰是男性针对女性作案,但从绝对数量上说,男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女性对男性的性侵扰同样发生得非常频繁。
事实上,无论依据哪个来源的资料进行统计,男性一生中遭到强奸(或其它类型性侵扰)的概率,都远远高于其遭到虚假强奸指控(或其它类型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概率——比如根据2015年的一份调查,美国男性有2.6%曾经遭到强奸或未遂强奸,24.8%曾经遭到带有身体接触的性暴力,17.9%曾经遭到带有身体接触的性骚扰[17];这比一名男性一生中遭到虚假强奸指控或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概率(遑论因此被错误定罪的概率),高出了不知多少个量级[18]。
然而在父权社会文化对性侵扰的刻板印象中,“男性遭到(无论来自男性还是来自女性的)性侵扰”的可能性却被下意识地过滤或屏蔽了,以至于当人们自动代入“男性中心视角”时,后者却并没有将性侵扰的男性受害者的视角(以及女性嫌疑人的视角)同时包括在内。
对男性受害者经验的过滤,凸显了父权社会传统性别角色模式所造成的偏见与伤害的双向性(尽管两个方向上的偏见与伤害程度未必对等):当女性被贬为“理性能力不足”或“狡诈不可信赖”的生物时,男性也被桎梏并压抑在“男子气概(masculinity)”的要求之中。
性方面的“征服力”正是传统性别角色模式中“男子气概”的一大体现,而性方面的“被征服”(既包括被性侵扰,也包括异性恋视角下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的“被插入”),在传统“男子气概”标准下可谓莫大的耻辱;性侵扰的男性受害者,也往往畏于外界对其“不够男子汉”的二重羞辱与攻击(一如女性受害者经常遭到“荡妇羞辱”),而不敢报案或向别人吐露自己的遭遇。
比如美国黑人影星特里·克鲁斯(Terry Crews)尽管外型硬朗、肌肉强壮,但当他在MeToo运动中曝光自己也曾经遭到好莱坞制片人的性骚扰时,却迎来了男性网民的疯狂围攻指责,认为他丢尽了男人的面子。
至于男性遭到性侵扰的经历之普遍程度,更是对“男子气概”这一迷思本身的巨大冲突;要维持迷思,就不得不在父权视角中过滤或屏蔽男性受害者的经验。
(2b)这种“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还有一种常见的变体,即“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
由于男同性恋的存在对父权社会的“男子气概”叙事制造了极大的困难[19],因此在性少数权益逐渐得到正视的今天,代入“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者便往往不自觉地将男同性恋的经验作为“特例”悬置一旁,以此使得“男子气概”叙事继续在“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e)”的话语框架内部不受动摇。
这种下意识的心态反映在对性侵扰问题的理解上,即是默认遭到性侵扰的男性都是同性恋,异性恋男性绝无遭到(不论来自男性还是来自女性的)性侵扰之虞。
换句话说,性侵扰的异性恋男性受害者的经验,在经由“排除同性恋特例”所得的“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中,仍然属于被过滤与屏蔽的对象(与此同时,这一视角也依旧忽略着“女性对别人实施性侵扰”的可能性)。
MeToo运动在鼓励大量女性受害者公开陈述自己遭遇的同时,也让男性受害者(比如陶崇园、特里·克鲁斯、张锦雄事件中的诸多受害者、被女教师性侵的男学生、被教会神职人员性侵的无数男童)的境况获得了公众的关注。
讽刺的是,当MeToo质疑者对MeToo运动表示有保留的赞许时,这种赞许往往却又出自“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对性侵扰受害者身份多样性的屏蔽,比如:〖如果一定要对#metoo运动做一个“好”或者“不好”的判断,我会说这是好事,因为它是一场教育运动,对男人而言,教育他们节制与尊重,对女人(以及某些男同)而言,教育她们(他们)自我保护,尤其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 say no或甚至报警。
〗(L.2)——可以看出,作者下意识地认为,性侵扰的作案者只可能是男性、不可能是女性;性侵扰的受害者只可能是女性和同性恋男性、不可能是异性恋男性。
(3)总结上面的讨论:对于“MeToo运动将导致性侵扰虚假指控与错误定罪的绝对数量增加,从而必将对某个无辜者的蒙冤负有责任”这种批评,应当如何看待?
其一,诚然,对于任何个案,我们都需要极其认真谨慎地评估具体证据,尽量避免无论假阳性还是假阴性结果的发生;但就整个系统而言,个案的假阳性判决,在任何类型的案件、任何合理的举证责任方案、任何合理的审判程序中均不可能完全避免。
在系统层面必须保障的,绝非不计后果地将假阳性概率一路降低到零(这意味着完全放弃司法体系的定罪功能),而是确定和维持(或者尽量接近)假阳性概率与假阴性概率的最合理平衡;这个平衡可能非常接近于假阳性概率为零,但绝对不会是等于零。
在父权社会的现实中,对女性证词的“可信度打折”使得性侵扰指控的证据评估存在系统性的偏差;人们对性侵扰受害者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加剧了这种偏差;受害者遭遇的社会敌意与羞辱(包括对受害女性的“荡妇羞辱”与对受害男性的“男子气概羞辱”)又令其中大多数人不敢报案。
凡此种种,都使得假阴性概率远远高出合理的范围,现状与合理平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
在这种情况下,MeToo运动鼓励受害者出面倾诉、鼓励人们更加信任倾诉者的证言,恰恰是将极度偏差的现状稍稍地往平衡点方向扳回一些,但也远远没到能够真正将其扳回平衡点的地步,遑论造成假阳性概率的不合理攀升。
这个过程中确实可能出现若干假阳性个案,对此我们只能通过具体证据评估中的认真谨慎来尽量防范;但倘若不同时竭力清除性别偏见在证据评估层面的系统性污染,单靠“认真谨慎”并无助于解决整个系统的产出结果高度失衡的问题。
其二,既然如此,仅仅出于对假阳性个案的恐慌,而否定尽力缩小现状与合理平衡之间系统性的巨大偏差的意义;或者至少在权衡二者的先后时,赋予前者(避免假阳性个案)不成比例的权重;同时又并未对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指控与错误定罪表现出同等程度的恐慌——这样的心态根本上是对父权社会“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的内化。
在“异性恋规范”的传统性别角色话语的潜移默化下,这一视角使得观察者下意识地过滤和屏蔽了男性(尤其异性恋男性)遭到性侵扰的可能性、以及女性施加性侵扰的可能性,再加上对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便导致了对“女性诬告男性对其性侵扰”这一极小概率事件的过分关注,以及对整体图景(包括现实与合理平衡之间偏离程度)的忽略。
一旦跳出这一视角的桎梏,即可发现,尽管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对此不成比例的恐慌,其实只是父权社会文化一手缔造的庸人自扰。
(后文从略,部分章节见:https://www.douban.com/note/864521253/ )[1] Philip N.S. Rumney (2006), “False Allegations of Rape,” Cambridge Law Journal 65(1): 128-158,第136-137页。
[2] Jo Lovett & Liz Kelly (2009), Different Systems, Similar Outcomes? Tracking Attrition in Reported Rape Cases Across Europe, London: Child and Women Abuse Studies Unit,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各国比例从低到高分别为:匈牙利1%(第69页)、瑞典2%(第100页)、德国3%(第62页)、奥地利4%(第34页)、苏格兰4%(第94页)、比利时4%(第41页)、葡萄牙5%(第85页)、英格兰及威尔士8%(第49页)、爱尔兰9%(第78页)。
[3] David Lisak, Lori Gardinier, Sarah C. Nicksa & Ashley M. Cote (2010), “False Allegations of Sexual Assault: An Analysis of Ten Years of Reported Cas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6(12): 1318-1334。
[4] Cassia Spohn, Clair White & Katharine Tellis (2014), “Unfounding Sexual Assault: Examining the Decision to Unfound and Identifying False Reports,” Law & Society Review 48(1): 161-192。
[5] Andre W.E.A. De Zutter, Robert Horselenberg & Peter J. van Koppen (2017), “The Prevalence of False Allegations of Rap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6-2010,”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ology 2(2), 119: 1-5。
[6] Liz Kelly, Jo Lovett & Linda Regan (2005), A Gap or a Chasm? Attrition in Reported Rape Cases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293), London: Home Office,第51-53页。
[7] Amy Dellinger Page (2008), “Gateway to Reform? Policy Implications of Police officers’ Attitudes Toward Rape,”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3(1): 44–58。
[8] Jan Jordan (2008), Serial Survivors: Women’s Narratives of Surviving Rape. Sydney: Federation Press,第214页。
更多类似案例,参见Jan Jordan (2004), The Word of a Woman? Police, Rape and Belief.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9] Jennifer Brown, Miranda Horvath, M, Liz Kelly & Nicole Westmarland (2010), Connections and Disconnections: Assessing Evidenc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Responses to Rape, London: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第40页。
社会文化及执法系统对熟人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与敌意尤其严重,相关分析参见诸如Michelle Anderson (2010), “Diminishing the Legal Impact of Negative Social Attitudes to Acquaintance Rape Victims,”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13(4): 644-664等。
[10] Crime Survey for England and Wales (2018), Sexual Offences in England and Wales: Year Ending March 2017, London: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11] Alison Levitt QC &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Equality and Diversity Unit (2013), Charging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Wasting Police Time in Cases Involving Allegedly False Rap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llegations: Joint Report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London: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第6页。
该报告标题及正文所用“强奸”一词,实际上包括其它类型的性侵扰,见第5页注5。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其间英国检方共起诉了111891起家庭暴力案、6起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3起虚假性侵扰指控兼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由此可知检方认定的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比例仅为万分之0.8(111900起中的9起)。
[12] 前引英国皇家检控署报告提到,2011至2012年间,在英国检方起诉的性侵扰或家庭暴力案件中,经由庭审成功定罪的比例为73%,见Levitt & Equality and Diversity Unit, Charging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Wasting Police Time in Cases Involving Allegedly False Rap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llegation,第2页。
不过从这一资料中并不能得知,庭审释放的嫌疑人究竟有多少确属遭到错误指控、有多少实为真凶却因证据不足而逃脱法网。
[13] 见前引Gross, Possley & Stephens, Race and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第11-12页。
[14] 参见Pam Oliver (1991), “‘What Do Girls Know Anyway?’: Rationality, Gender and Social Control,” Feminism & Psychology 1(3): 339-360;Miranda Fricker (2009),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Deborah Tuerkheimer (2017), “Incredible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the Credibility Discou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66(1): 1-58等。
[15] 比如参见Amy Hardy, Kerry Young & Emily A. Holmes (2009), “Does Trauma Memory Play a Role in the Experience of Reporting Sexual Assault During Police Interviews? An Exploratory Study,” Memory 17(8): 783-788;Michele Bedard-Gilligan & Lori A. Zoellner (2012), “Dissociation and Memory Fragmentation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 Evaluation of the Dissociative Encoding Hypothesis,” Memory 20(3): 277-299等。
[16] 比如根据前引英格兰及威尔士年度犯罪报告,强奸受害者中女性占88%,男性占12%;其它类型的性犯罪受害者中女性占80%,男性占20%;见Crime Survey for England and Wales, Sexual Offences in England and Wales: Year Ending March 2017,第11页。
另据全美伤害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一份调查,在遭遇过强奸的女性中,98.1%只被男性强奸过;在遭遇过强奸的男性中,93.3%只被男性强奸过;参见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0),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2010 Summary Report,第24页。
其它报告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不再赘述。
[17]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5),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2015 Data Brief – Updated Release,第3页。
[18]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前引诸多关于虚假性侵扰指控比例及错误定罪数量的研究,结合所在国家的成年男性人口数量,自行换算相应比例。
[19] 参见Michael S. Kimmel (1994), “Masculinity as Homophobia: Fear, Shame, and Sil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 in Harry Brod & Michael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London: SAGE,第119-141页。
8 ) 向左看向右看都是女观众时,我们过去现在未来始终需要这样“直白”呐喊的感觉尤其强烈
还是先废话一些我看这部电影的前提,日常几乎不太关注舞台剧、话剧这类在剧场演出的作品,我确实从未听说过《初步举证》。
看之前我只知道这是一部由朱迪·科默参与的,剧场演出的官摄版本,和法律题材有关的作品,以及涉及到女性议题,其他一概不知。
对于提前知道,甚至看过剧场版本的观众,大概能想象我这种会经历怎样的观影心路历程——天呐,开头的台词也太密集了吧,这台词怎么背下来,舞台剧对演员这方面的要求真是太强了。
这么密的台词我真的会有点跑神诶……以下是按照观看全程我实时冒出的感想,全程剧透请注意——虽然不是所有台词都看到记住,我能看出来这一段是在树立女主人公作为刑事案件辩护律师,业务能力超强的“强人”人设。
哦好,接下来就要介绍女主家庭背景了,没提到爸爸,好像有点重男轻女家庭里长大的,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夹在中间的那个女孩。
等下等下,所以整出剧只有朱迪·科默一个演员,居然是全程由她自己口述和表演的独角戏啊……啊,求学背景,加了“英国小镇女做题家”人设。
向左看,向右看这里,因为逗趣的表演和讲述,能在其他密集的台词中,留下深刻印象。
啊,女主背景交代完,职场时刻现在进行时。
去Pub玩那里感觉有点“不对劲”诶,搂腰,和亲脖子,难道不算性骚扰吗。
好吧,如果是互相看对眼的办公室恋情,前面的就当是恋爱铺垫了,但亚当搂腰不算性骚扰吗。
(我有点记不清跟泰莎职场“恋爱”故事的前后顺序)提到为性侵案被告辩护时,女主人公作为“女律师”的优势,以及那个“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让更多的女性不受到侵害”的被害人。
从讲述,到舞台重点放在卷宗上灯光,有“不好的预感”。
从泰莎和那个男的喝了不少酒,回到自己家亲热,和前面她为被告辩护的性侵案如此相似的展开,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并不是吐槽这种剧情上的所谓没有悬念,反而我作为观众,从身体到精神都开始进入一种紧绷状态。
然后,是一场雨,直接下在舞台上的雨。
接下来,是全程仅出现三次的音乐时间,DAY的数字不断跃动,从1到100,到200,到500,最后停在782。
我眼泪哗就下来了。
我会哭,是因为想起我这两天刚听完的独树不成林播客第184期节目《在美国忍受诬告是什么体验?
》中,播讲人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什么事都没做错的彻头彻尾的受害者,在面临背叛她的两个人发起的诬告官司中,为了应对司法程序和校方审查,而对自己生活、事业、人际关系全方位的摧毁。
我也想到我身边认识的一个女生,历经两年的时间,终于在前阵子尘埃落定的离婚官司,在这段不算很长但也绝对不短的时间里的经历。
以及之前看过的印象深刻的、快忘记的或真实或虚构的性侵案件中,当一个被侵害的女人决定从法律层面惩罚强奸犯,必然要面临怎样残忍的、羞辱式的,一次次揭开伤疤的痛苦。
而这些,也的确由再次登台的泰莎告诉了观众。
之后从报案、到接受身体检查、再到把一切告诉妈妈、以及法庭戏,我基本全程都跟着剧情和朱迪·科默的表演走。
我注意到,之前仿佛作为“罐头笑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台下观众们,终于在泰莎总结陈词阶段,让作为电影观众的我看到了。
我第一反应是:这个剧场很小,舞台也好小啊,观众距离舞台和演员居然这么近。
官摄镜头从这里开始,不再只是拍舞台全景和朱迪·科默的面部细节,而会偶尔投向台下的观众们。
我参加的是全女观影团,电影结束后还有观众的映后交流环境,女孩子们很健谈,聊了许许多多不同角度基于电影的感想。
后来我想,如果我发言呢,我想跟同场观看的女孩子们分享什么呢?
会想聊一聊司法程序的繁琐,以及漫长的时间对人全方位的折磨,聊播客独树不成林的树老师, 我那个终于离婚的朋友。
会想告诉大家,尽管如此繁琐、折磨和痛苦,但还是要坚持,如果不经历这些,如果不去抗争,不去争取,那些本该属于自己的,可能都得不到。
会想提一下前段时间徐娇的室内禁烟事件涉及的关于个人(尤其女性)权利边界的话题;会想说说最近围绕林奕含作品一个很奇怪的讨论方向“弱女”。
会想说,《初步举证》里的泰莎绝对是“强女”的代表了,尽管剧情里也用她在事发后无措地洗了澡,茫然地离家走在街头,气愤地删了短信,这些让她事后骂自己蠢的第一反应,刻画了她“弱”的一面。
想聊一聊,何为“强”与“弱”,如何看待“强”和“弱”。
强和弱的行为,似乎可以清晰地划分:仗义执言的是强,唯诺忍让的是弱;果断冷静的是强,惊慌失措的是弱;不哭的是强,哭的是弱……但谁也可能一比一地按照并不存在的《女强者行为指南》实践,总有踏错的时候,懦弱的时候,妥协的时候,退却的时候,甚至完全放弃的时候。
人,总是更倾向慕强的,文艺作品如此,所以独角戏的泰莎一定要是这样的角色,无论她在过程中犯了多少错误,最后她一定要掷地有声地呐喊出自己身为专业法律工作者以及受轻视、侵害、污蔑的女性的声音。
最后泰莎的陈词是那么直白:现行法律是男性为主修订的;性侵案从法律思维要求逻辑的严丝合缝,与受害者作为一个人类,在自己身体遭受兼带毁灭精神的侵害时,无法在被侵害时及以后如此精准地回忆并保存证据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
性侵案维权的一系列法律流程,都充满了对女性受害者的不尊重。
这些观点当然不新鲜,不出挑,不惊世骇俗,无论在相关主题的文艺作品,还是社会上出现较大规模讨论的真实案例中,都能听到类似的声音。
但我们现在还很需要这样直白地、大声地、铿锵有力地、一遍又一遍地说出这样的“问题”。
不过我本人,反而为这个法律议题陷入某种矛盾中。
上面我提到独树不成林的树老师,在她被诬告的官司尘埃落定后,决定不反诉诬告她的两个人,让一切成为过去。
当然不是因为她大度,播客最后她也分享了和自己博导之间关于法律的讨论,博导是这么劝她的:不要把法律制度的公平,和个人意志的公平混在一起。
现代正义制度的制造者告诉我们,制度层面的正义不是由个人判定的,法制就是为了提供中立的第三方,且是非个体的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只在乎制度的公正,而非个体的。
公民社会,个人把判断正义的权利从制度上让渡给第三方。
不能从法律层面追求个人复仇和个人正义,只有保护好自己,不要让他人侵犯自己的权利,不要让渡自己的权利。
我在想,《初步举证》的编剧借由女律师“泰莎”之口,说出性侵案判定从法律思维的不合理之处,那么其他类型案件的判定呢?
如果法律对所有罪名都要求的逻辑链条的严密,在某个性质的案件中,可以由其他认定方式取代,那么其他类型案件要从什么层面去成为法律思维的特例呢?
而当我意识到我这么思考时,我突然背脊发凉,觉得自己实在太置身事外的冷血了。
因为我是那个“向左看”“向右看”中,几乎没太受过此类伤害的女性幸存者。
所以我才能如此“冷静”地以所谓中立视角,去讨论法律中的问题吗?
还是我始终待在我不自觉的社会“强者”地位,而不自觉地对“弱者”诉求感到“对方感情用事”吗?
对,泰莎是“弱者”。
尽管舞台表演中不断用表情和台词,去塑造这样一个面对为自己以及不计其数的女性受害者争取权利的“法律强人”。
但泰莎毫无疑问是“弱者”是一桩从开始就极大概率失败的案件的弱者,是一个对乡村女孩从家庭到求学各种歧视的社会中的弱者,是一项男性从业者占据多数及高位的行业的弱者,是从法律制度层面从决定为自己寻求公平正义那一刻起就注定的,弱者。
我的大脑在各种观点的打架中,已经得不出什么关于强和弱的结论。
我在电影落幕时,在戏中的泰莎以演员朱迪·科默的身份接受观众雷动的掌声中,我开始哭。
我为这个虚构故事中的“泰莎”哭,为我居然第一次知道“三分之一”这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哭,我为现实世界中经受真实苦难的“泰莎们”哭,为我为什么不能坚定地同意这部作品传达的法律观点哭。
我为能看到这样的作品而开心,又为具体的故事而难过,同时还为其中的表达而纠结痛苦。
这便是,优秀的作品了。
9 ) “以强始、以和终” “以和始、以强终”
形式很新颖,全靠一名演员的独白撑起全场,像是独角戏或者某种脱口秀。
别说演,看下来都累。
讲述的内容呢,是一场“炮友”间的酒后强奸案,走了司法程序,但证据不足,陪审团认定被告无罪。
这种事例应该不少,类似的还有婚内强奸,法学领域各种案例和研究都很多了。
这位主创好像真是学法律出身,干过刑辩律师。
但结尾提出的解决思路,真的没有可操作性。
她说现在立法司法里,关于强奸罪的内容都是男权视角,应该换成女性受害者做主。
那到底该怎么操作,还是让人想不明白。
司法实践上千年积累下来这套做法,是靠天量的各种案例,从各个角度摸索出来的执行边界,它考虑的要素,不止是惩治罪犯,还要防止人利用法条设陷诬告,仙人跳做局等等。
所以司法只能看证据。
有人说,应该以受害者的心理评估为准,但心理评估的本身没那么客观,不同的人又千差万别,很难真正操作。
关于男女之间的强奸,清代刑事案例集里面已经有很多种,它区分的是“强”与“和”(两性的同意)这对概念,实际案例侧重插入阶段是否一直形成和意,有“以强始、以和终”的,还有“以和始、以强终”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更别说还有玩这方面游戏的,没法一刀切。
所以司法体系不是万能的,涉及难以确切举证的私密时空,难以完全指望司法。
但司法难以触及到的地方,才是这类作品的价值。
首先得有人站出来讨论,才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在道德层面上起到警戒作用。
另外,人们以后对于性的耻感降低了,习惯公开谈这类事情,也会好得多。
不过耻感又是跟刺激程度呈正比的…
10 ) “法律是由一代代的男性建立的”—初步举证
完美的无可挑剔的科学的正确的最伟大的剧之一。
应该被列为全世界成年人必看剧,不看不许成人。
最让我感到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是:当我以性侵受害者站在证人时我才明白,要求性侵证据清晰完美逻辑严密这一法规是完全有问题的,法律是由一代代的男性建立的。
这个世界的女性远远没有到可以说向下自由的那一天,这一代代由男性建构的法律体系需要我们修正,这一代代全是男性的派出所、法院、检察院、陪审团再无法容忍了,就像RBG说的那样,十二个大法官全部都要是女性才行,全部都要!
不战斗,等待我们的就只有蹂躏和死亡!
面对性侵,女性在事后除了做尽可能完整的证据留存等事后措施,在事前推动法律上、教育上程序正义修正,更要学会锻炼出足以防身的体格。
就该向冰岛那样,早早的鼓励女性更多尝试过往被定义为男性主导的格斗比赛,鼓励男性从小学会共情和感性思维。
女性没有时间休息了,她们必须从小摒弃所有玫瑰色的幻想,要明白,她们先天在体格上弱于男性,并且因此随时可能被摧残,在达到力量平等前她们绝不可能和男性有自由的性爱,她们的命运必须抓在自己手中。
在性爱中,只有男性发自内心的明白她不可能被他压在身下任他蹂躏,才是最根本整治性侵的手段,他们会通过女性的力量明白什么是No的。
双方再有智慧头脑社会地位的平等,在最原始的性爱中都无法消弭力量差距,没有任何时刻比此刻更想学会打拳。
要想夺回国家之间平等对话的自由,只有国防科技力量上的相对平等才能做到,千百年来的教训都告诉我们力量的落后会带来多少灾难,女性怎可放任自己生理力量低人一等!
所以在客观差距无法消弭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异性恋,就像不能让小女孩和成男恋爱一样,不能让下属和上司恋爱一样,不能让学生和老师恋爱一样,没有权力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爱情,同性恋是这个时代女人的宿命!
我没有那一刻比现在更恐异性恋,在千百年来的男权社会里找寻自由平等的爱情无异于粪中找花。
在达到力量上的平衡评估前应该禁止结婚,当然婚内强奸的判定也必须完善。
身为女性,我们要做的还有太多。
法律一直以来维护的是男性眼中的正义,我们努力必须让法律看向所有人。
“一些大律师从中央刑事法庭专程赶来看这部剧,她们提出了TESSA提案——《对严重性侵犯的质询方法提案》,并向政府提出异议。
还有中央刑事法庭的一位女法官,她将这部剧定为法官上任的必修剧目。
所以在法庭上,证人经历是公诉人必须听取和考虑的内容,而不是仅凭当事人对性侵经历感到困惑,或者证据不足,就妄下断论当事人在捏造是非。
这是极端离谱的。
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发现了这一点,我是从现在、当时的记忆和我们对生活的情节化阐释三个部分,来构建剧作结构的,女性对创伤的叙述与既有法庭更倾向采纳的证人证词是如此迥异不同。
”——编剧Eve·Ensler“从源头来看,将男人与男孩置入讨论中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们需要成为对话内容里的一部分,也需要支持这场运动,否则改变寥寥无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需要站在我们这一边,对他们的性别教育需要被看见,每一件小事都至关重要。
……法庭上的庭审宛如儿戏,他们并不想弄清楚真相,只想得到他们想要的法律真相。
性侵相关法律的重点,往往会集中在男性身上,女性作为受害者负有精神难以承受的举证压力,传统上都是从男性嫌疑人有没有被诬告的视角出发,来自全社会的羞辱都加在了性侵受害者的身上,仿佛这原本就应该让她们承受,这是她们咎由自取的结果。
我想这部剧能够拓宽视角,让人们看见并且不带羞辱和恐惧的自由讨论女性受害者的感受,这件事实际上的全社会的羞辱,而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创建一个更适合处理这类问题的对话机制,我希望由此能够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们中间建立这种意识。
包括在学校系统中谈论性同意,我想这是能够取得改变的唯一方法。
一旦我们开始讨论这些事情,你就不能假装它们并不存在。
这个社会一半由女性组成。
”——Soma(反强奸文化运动组织者)摘录自初步举证百老汇公演后编剧发起的圆桌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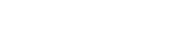



























印尼驱魔片一如既往的廉价血腥母亲为救疯癫入魔女儿四处寻找解救之法狗血家族爱恨情仇祸及子孙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反而去残害无辜面目狰狞龇牙咧嘴各种血浆飞溅残肢断臂最后结局为保女儿牺牲自己好一出感天动地的母女情深剧情真的换汤不换药过于套路
剧情太烂,白瞎了这么多演员,电影里看到很多印尼恐怖片的熟面孔演员~
什么玩意!就不能冤有头债有主,直接找那个渣男报复啊!
1:37:22
1:3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