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飞的女孩》剧情介绍
影片讲述了一对表姐妹二十余年的成长与救赎:拼死逃离毒窟的田恬(刘浩存 饰)走投无路,前去寻找已决裂五年的表姐方笛(文淇 饰)。但此时,为了生存和梦想已伤痕累累的方笛并没有做好接纳表妹的准备。随着犯罪分子的步步紧逼,姐妹二人命运的齿轮不得不重新咬合在一起……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汶川儿女苍天洗冤录2社长室之冬:获得巨大新闻社的男人贫民区牛仔拉字至上第三季珠帘玉幕哑孩儿吞下宇宙的男孩台北十日利剑行动革命机Valvrave阴错阳差第二季精卫填海女演员大作战形如父子死人的鞋子叛我更幸福陨石江湖:天降20亿逆鳞真实亲爱的,看招弗里达穷途鼠的奶酪梦深宫遗梦之美人赦世界将颤抖疯狂的爱十四天一切都好断头气
《想飞的女孩》长篇影评
1 ) 谈谈作为电影插曲的《渔光曲》
《渔光曲》是文晏导演的电影新作《想飞的女孩》里的重要插曲、也是近百年前问世的重要左翼电影《渔光曲》的同名主题曲。
1934年问世的这首《渔光曲》,讲述了同名电影里沿海渔民忍受饥寒与压迫、终日不得安生的真实故事。
正如3月23日下午文晏导演在电影《想飞的女孩》南京站放映中所说,本片跟《渔光曲》类似,同样把浙江象山作为重要拍摄场地;把《渔光曲》选为电影插曲,不只是对中国百年电影史的尊重,也同样是以犀利而凛冽的电影语言表达,来向当年以蔡楚生、郑君里等为代表的电影人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做致敬式对话。
耐人寻味的是,电影《渔光曲》里渔民遭遇的穷困、卑微与被剥削,在代际之间的宿命般传承,同样跟电影《想飞的女孩》里、姐妹俩拼尽全力、也难以挣脱原生家庭的悲剧性影响的主体故事之间,构成一种更深层次的互文关系。
正基于此,那些指责文晏导演把矛盾冲突聚焦于家庭内部、而忽略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的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正如《渔光曲》里渔民的穷与困、从来不是或不只是渔民自身的问题一般,在电影《想飞的女孩》里,无论是父亲冲动杀人指向的权力寻租与社会“潜规则”、还是姑姑工厂经营不利与持续欠薪对越发充满不确定性的大时代的隐喻,都跟其致敬的《渔光曲》一般,有着明确的时代关怀与现实敏锐度。
夜已深,回味《想飞的女孩》里那些惊心动魄的电影场景,再想起五年前“困居”家中时、仔细拉片《渔光曲》时的感怀莫名,还是要为文晏这样坚持作者表达与田野在场感的电影创作实践,大张旗鼓地叫好。
2 ) 如果世界是海洋,女孩就是溺水的鸟,想飞的女孩是乌鸦。
这部电影里的女性总是溺在水里。
姑姑溺在家庭作坊的水里,被弟弟、丈夫、父亲和债主黏住,无比压抑又永无尽头。
方笛溺在影视城外的河里,绑着铁锁,混着经血,衣服浸满冷水,身体越来越重。
田恬溺在晨光下的海里,海水一遍遍冲过,直到将她淹没,带入死亡。
《烧女图》里也有类似的溺水戏,在女主去孤岛的路上,而从孤岛往外望去,广袤世界是男人之海,对女性而言,那里海面闪着阳光,实际幽深而冰冷,从古至今始终如此。
而生活在父权世界的女性,总是像出生于海里的鸟,这里为鱼打造,不为鸟。
你要么努力去飞,要么沉入海底。
但沾水的翅膀,展动时又何其艰难。
想飞的女孩被认作是乌鸦,是不详的巫女。
下海年代里想飞的姑姑,在酒局里被性侵而坠落,自诩拯救者的弟弟,将她称为不详的人。
此后她不再试图去飞,在负罪的人生里作茧自缚。
目睹悲剧的方笛不想飞,她从重庆逃亡北京,只是从地狱逃往另一个地狱,依旧被铁锁和沉重的水束缚身体,失去姓名。
怀抱着乌鸦的田恬,更早地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带着无尽的勇气,十七岁的她决定堵一把。
她努力振翅,然后失败。
望着天空,望着清晨的太阳,田恬在海水中死去。
而此刻的方笛,终于看到属于女孩真正的悲剧。
在士兵们的围攻中,她最终从城楼跃下,决定从此开始真正去飞,像一只乌鸦。
即使是乌鸦。
属于女孩的世界在天空,那是另一场游戏。
这是一对姐妹的故事,是两代女性的故事,也是所有女孩的故事。
不要沉默地溺入那片深海,你是扇动翅膀的金乌,你是想飞的女孩。
3 ) 嘲笑狗血的情节是否也是一种漠视?
我似乎有点get文晏导演想表达什么,方笛试戏的时候已经表现过了,那些矫揉造作的台词和汹涌的浓烈的爱恨情绪是惹人发笑的。
观众们在短视频和短剧的轰炸之下,图新鲜图乐趣图刺激,到,甚至麻木了。
当遭遇生活中真实的苦难时似乎有这样的错觉:好像也还好吧?
好像你也没多痛苦啊?
好像你还不够惨啊?
所以这对姐妹便在其中扮演了最狗血最脸谱最无聊的故事中的主角,似乎人人都能看着她们笑出来,多蠢的两个人,多老的套路,多无聊的剧本。
未成年生子等现象跟着后撤了一步,变成远方的酥烂的惹人发笑的故事。
“真的吗,我不信,哪有这么夸张啊,哪有这么惨啊,不至于吧哈哈哈哈…”这是布里抽出来的一根晶莹的丝,只可惜整张布已破碎。
出戏和入戏本来可以大作文章,不知为何只用来表现借用威亚来飞这一个桥段,倍感失望。
4 ) 复写的命运
重复,或者说复写,是解读《想飞的女孩》的一个关键。
在这短短几天,但又贯穿二三十年的时代叙事中,我们能看到很多次不同意象的“重复”。
在这些对不同概念的复写中,由方笛和田恬命运所牵引着的主题一点点浮现。
它们就像身为武术替身,一次次被投入水中,最终却根本不会在银幕上出现的方笛所经历的那样,一些人,一些事,始终在历史的波纹中重复着,但他们的身影却始终在其中隐没,如同方笛一次次没入水下,那是女性们,不同却相似的悲剧命运。
文淇在片中饰演的武术替身方笛,可以说就是一个始终在重复着不同动作的角色。
“重复”就是她这个角色的关键词。
因为武替做的,往往都是那些难度高的、或者主角不愿意做的动作。
难度便意味着重复,于是在她出场的第一个飞上屋檐的镜头里,我们看到她也重复拍了好几次,才完成了这个动作。
在这个场景里,她的确是在“飞”。
但这一次次的飞,更像是被身上的威亚所穿透、所束缚、所控制的,提线木偶般的行为。
那并不是飞。
很明显地,那场同样被数次拍摄的生理期下水戏,也是一种“重复”,由于方笛的拒绝,这种重复甚至带上了某种惩罚的意味。
方笛的梦想当然不止是做个武替,她想成为一位演员。
但成为演员以后就会更好吗?
影片用一场非常讽刺的戏,为我们暗示了答案。
在唯一的一场,方笛最接近演员梦想的试戏场景里,方笛也“重复”表演了两次。
可那些姐妹相争的戏份显得是那么的虚无和荒唐。
即便是站在一旁偷看,对表演毫无经验的田恬都能够从这枯燥的表演中感知到,这是毫无意义的“重复”。
但电影不就是由许多无意义的“重复”构成的吗?
留在银幕上的那些时间背后,是演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们反复调试出的精准,他们一遍遍在重复中蒸馏出的,是有关电影的那些决定性瞬间,是会被我们记住的有意义的时刻。
于是,这些“无意义”的重复在叙事中便构建出了关于重复的“意义”,那是方笛所谓梦想的虚妄,也是影视城的虚假浮华的虚妄,而对于电影拍摄带来的那些隐形的、幽灵般的、从来就不可见的无数的重复来说,《想飞的女孩》,也由此完成了它对电影本身的自反。
同样的“重复”,还发生在田恬的命运里。
她受累于父亲的过去,因此被犯罪团剥削。
她也受累于父亲的现在,始终逃不开被父亲吸血的困局。
她显然也在重复着父亲的悲剧命运,父亲是弟弟,在能干的姐姐面前,是家里不成器的最小的那个。
而田恬自己,也仿佛复刻般成为家中最小的、也最差的一辈。
这样的她,还未婚先孕,生下了最小的女儿露露。
无需多言,露露显然也会重复她母亲的悲剧命运。
就像乌鸦作为田恬这个角色的意象,反复在片中出现,甚至还被田恬纹在了自己身上,她身上从小到大始终存在的红色元素,乌鸦的黑色不详,女儿的未来,都是她这个人物命运的“复写”。
从田恬的“红色”开场这是个很残忍的现实,对那些始终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挣脱这种命运,可能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积累。
回头去看影片那段用画幅区隔开来的90年代叙事,就会发现故事并没有太大不同,上一代的悲剧命运,让这一代身上的复写显得更为清晰了。
方笛母亲是那个撑起整个家族的人。
她开设服装工厂,在重庆朝天门市场、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之一兴起的年代,她是那个走在前面,愿意去赌一把看看的人。
她不仅养大方笛,照看弟弟,甚至还一同养大了田恬。
但就是这样一个主心骨女性,在影片的大多数时间里,整个人就像淹没在逼仄的家庭作坊空间和布料的阴影中,我们甚至都不太能看清她的脸,换句话说,她淹没在劳作中,也隐身在家庭历史中。
方笛母亲的家庭作坊于是她也就成为了所有人。
就像无数同样淹没在家庭命运中的女性——那些曾浸泡在厨房里,从未被看见的女性;那些在扶养中被剥去了自我,只拥有母亲身份的女性;那些即便职业有成,却仍旧被要求母职、妻职,才能被认可的女性。
饶有意味的是,就连方笛母亲“疑似被性侵”这件事,也是隐没在叙事中的。
故事中的人们,尤其是她自己,都没有正面提及这段创痛。
唯有弟弟在彰显自己为这个家牺牲了多少的争吵中,才隐晦地提及自己是曾因此为她出头,才导致入狱。
可笑吗?
当一位女性足够强大,她就可以被整个家庭榨取。
而当一位女性不够强大,她所遭受的伤害,又成为了这个家庭悲剧的来源。
而当她真的失败,那世界又最乐于看到这样的受害者,因为所有的责怪就都因此有了去处。
方笛母亲的这一代,也是曾经试图挣脱命运的。
但悲剧仍在重复。
影片最后,方笛穿着田恬的红毛衣回到“家”,那个被搬空的服装作坊,对着母亲说“田恬安顿好了,露露我要带走”的那个时刻,就是三代女性的命运共同体,依然被困住的时刻。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想飞的女孩》试图描摹的,是始终隐秘发生在时代与城市的历史命运中的,那种悲剧、困顿、无法摆脱也难以跨越阶级的,属于小镇工民商阶层的代际传递。
优渥与精英的人生可以被复制,被再生产,贫穷与悲剧也是。
这种在不同代际间传递、复制、复写的命运图谱,已经近乎微观人群的时代史。
方笛的父母一代,差不多是六零年代生人,在八九十年代正值青年。
他们有一些眼界,有一点触角,还有很多勇气,但他们所能触及到的,大概只是时代浪潮的余波。
于是他们跟着浪潮冲进重庆的朝天门服装市场,拿回一些样衣,在家庭服装作坊的逼仄空间里打板、做样、跑货,或许暂时借着潮汐在高位看到过那么一点点的海平线,却又很快被浪头抛下来。
属于他们的空间,始终还是“家庭”这个空间而已。
这个空间曾经变成工厂,却又很快被搬空,流进过一些财富,却又很快分到更底层的工人们手中。
就像片中,那些本来要离开服装工厂,却在看到方笛母亲手里成沓的现金后,又坐回缝纫位上的女工们。
无论时代和投机曾赋予这个空间什么样的可能和意义,它都改变不了贫穷的本质。
方笛和田恬所代表的新一代女辈,其实也是一样。
她们曾试图走出去,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
这些方式或许有些粗暴,就像方笛身体力行想要实现演员梦。
这些方式或许有些笨拙,就像田恬想要生下女儿来重新开启人生。
但她们,是在往外走的。
在这些往外走的时刻里,她们曾经上山下海,却还是被困在麻木的躯壳之中;她们不是没试过升上高空或是沉入水中,但那所谓的磨炼或努力不过是世界为她们打造的幻梦。
就像方笛和田恬最后躲藏的那个影视搭景山洞,暂时安全,“像梦一样”。
最后想来说说的,是“幺儿”这个词。
我自己是四川人,影片的故事发生地是重庆,幺儿这个词,是川南地区对家中最小孩子的称呼,可以是女孩,也可以是男孩。
电影开始和结尾的最后一句台词,都是“幺儿”。
这个呼唤家中最小孩子的词语,却在一头一尾和影片中段反复出现的场景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味。
开篇,是犯罪者用“幺儿”这个词来叫醒田恬,温软的词汇却仿佛是地狱。
故事中间,田恬的父亲找上门来索取,大叫着“幺儿”,却只会让人觉得恐惧。
影片的结尾,一切回到开始,刚出生的田恬被带回家,彼时刚刚明白“爱”为何物的小方笛,试探着对这个小婴儿喊出了“幺儿”这个词。
因为她的到来,“家里最小的孩子”这个身份发生了转移,方笛成了姐姐,也就成为了现在时间线下,田恬向方笛求助的开始。
多么唏嘘,这样一个意味着血缘纽带的词,可以在这些重复中生发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
它既可以意味着拯救,也可以意味着毁灭,就像家庭关系在困顿的生活中既可以是生息之光,也能够释放出碾碎我们人生的摧枯拉朽之力。
所以,方笛最后告诉母亲,自己要带走露露抚养,不就是又保护了新的一代“幺儿”吗?
对于自己生活都已经如此困顿的方笛来讲,我们很难说,这会不会又是新一轮破碎女性的命运重复。
但这不就是“她们”面对明天的力量吗?
就好像文晏此前在《嘉年华》里,也让小米飞驰在前途未卜的公路上。
明知路的尽头已无去处,她们还是要上路;明知前面是废墟,她们却还要向山海迈进;明知已经身陷囹圄,她们,却还憧憬着要去看一场日出。
5 ) 是苦难还是疼痛表演,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女性故事?
首发于个人公众号: 特伦鲍姆的火箭 看完《想飞的女孩》后,脑中一直回想起弗里达的一幅自画像《断裂的柱子》。
1944年,她接受的脊柱手术让她需要长期佩戴钢制的支架来支撑身体,在病痛的折磨中,她以此创作了这幅画作,画中赤裸的身体被钢钉刺穿,裂开的胸腔中矗立着断裂的希腊柱子。
对于弗里达而言,这是通过颜料缝合肉体的手术,她将自己比作基督受难,钉子和断裂的柱子表达了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苦楚。
《断裂的柱子》这幅作品所包含的,是女性艺术家将私领域身体经验带入公共艺术领域的尝试,也是弗里达作为个体,对苦难的极致承受与顽强抗争力的体现。
可以肯定的是,艺术史从不排斥展现苦难,因为矗立在《断裂的柱子》前的观众除了观赏痛苦的美学转化,也能从众汲取到创作者的力量。
提弗里达,因为这半年看到了太多“女性疼痛表演”。
她们和弗里达的自我展示不同的是,尽管打着女性主义标签,但大部分陷入了某种怪圈:只有女性角色越是遍体鳞伤受尽折磨,她才能越快成长越够强大。
《国色芳华》里的“独立大女主”何惟芳,像柯南附体一样,不断底被陷害,被虐得体无完肤,虽然剧作打着女性互助,女性自我成长的标签,但为虐而虐属实有些疲乏。
近期的现偶剧《难哄》中的温以凡,真真堪称山城富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身边的男性爱上,其中大部分都不怀好意,几集一次的强奸戏,因为引起观众的不适,也在热搜上挂过几回。
虐女成为了固定景观,女性的成长似乎必须要跟极端的苦难挂钩,而苦难也正经历着诡异的“通货膨胀”,只要不把角色逼到绝境,就拍不出“有深度”的女性作品。
苦难和疼痛可以被展示吗?
答案是当然可以,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展示疼痛,而是创作它的人如何对待苦难和疼痛。
我对2017年上映的《嘉年华》评价非常高。
(指路一篇我八年前写的《嘉年华》评论《嘉年华》)《嘉年华》剧作和口碑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话题性事件与当时女性议题刚刚萌芽需要点燃的环境,恰如其时的迎来了这么一部作品。
但最关键的,依然是电影本身的好。
《嘉年华》的好,好在冷静、克制,却饱满且充满力量。
暴力并非只有被展示,从能达到惩戒暴力的目的。
疼痛和苦难也是一样。
未成年少女遭遇性侵,这是一个沉重的议题,但影片从始至终没有展现过犯罪者的面容,或者回溯犯罪的过程,去裸露受害者的伤口,而是不断质问警察、家长、医生等“旁观者”的共谋,将个体悲剧上升为集体与结构的反思。
时隔八年,文晏导演带来的这部《想飞的女孩》,依然是女性标签,女性题材。
电影中表姐妹的“救赎”建立在吸毒、未成年怀孕、替身女演员生理期受虐等极端化情节上。
针孔、淤青、血液,苦难必须经过符号的认证,才配看见。
这类叙事将女性的苦难简化为一种“成长仪式”,女性完成自我觉醒,或者实现互助的友谊,必须经历过肉体的摧残命运的毒打,疼痛必须裸露给观众,才能控诉与蜕变。
这样的猎奇操作与何惟芳、温以凡们如出一辙。
实际上观看她们苦难的观众们,就像那些去印度贫民窟观光的游客们,他们隔窗如同参观野生动物园一般去凝视贫民窟的生活。
这种“苦难凝视”与《想飞的女孩》的创作逻辑同构:它们都把底层封装成可安全观赏的景观,只震惊与同情,但没人叩问这样现状的病灶究竟在哪里。
《想飞的女孩》中贴满吸毒、堕胎、暴力等标签,但无一触及社会病灶,真正的施暴者,无论是个体还是结构,都隐身在了黑暗当中,草草收场,重庆的历史变迁也沦为了背景板。
诚然,电影描摹的是底层的故事,底层一直有苦难,但苦难并不意味着必须奇观化。
《小偷家族》中的临时家庭,每个人都在阴暗与夹缝中挣扎,而家庭中的每个人都直接关联着一个社会问题:养老、虐童、家暴、色情等等,这些所有问题聚集成了最后的小偷家族。
但这样的问题家庭却又是日常、生活的,却又是深刻的,通过电影叩问着社会福利系统的崩坏,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直至病灶。
当真相揭开时,大家才发现原来希望搭建在废墟之上。
真正的底层叙事,不在展示他们失去什么,而在呈现他们如何用废墟搭建希望。
但电影中,表姐妹情谊的救赎依赖外部危机,为了堆砌类型元素推出了莫名其妙的三人杀手组合,以他们的追杀推动姐妹情感化解。
片子在类型与现实间跳跃,似乎什么都想抓住,却最后什么都抓不住,越到后面甚至越能感受到创作者本身对这个作品本身的无力,与角色一样被困住了,困在了“受难-救赎”的故事牢笼里面。
2017年到2025年,八年时间里,欣喜于大众愈来愈多的看到了女性议题,看到了问题,但真正饱满的女性故事却少之又少。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女性故事,需要什么样的女性友谊?
是要展现女性苦难然后高举女性主义大旗,还是要化身社会议题的传声筒。
或许答案还是要回到最本质的追问:无论是精英、中产还是底层,她如何在与世界的碰撞中确认自我?
或许只有当银幕上的女性不再需要以苦难或者疼痛证明自身存在,当她们的觉醒可以源自一次平静而又日常的对话、一个微小的选择、一段未被奇观化血泪化的女性互助的友谊时,我们或许才能看到真正的“女性故事”。
6 ) Berlinale2025首映场:拍得有点太搞笑
(首发于「陀螺电影」)插叙的段落意指快速发展社会所留下的罪恶滋生的现状,可惜呈现得过于抽象,对于影片也许必要,却始终找不到合理的现实面向。
对于这些段落,影评人Nanako认为他们被使用得过多,导致影片有些混乱。
事实如此吗?
影片每次进入闪回其实都已经把握到当下叙事情节“需要发生中断”的时机,不顺势进入另一条线索,就会陷入紧绷而尴尬的状态,无法动弹。
不过这种时机的把握无法看为导演自觉的调度。
不像《嘉年华》谨慎而有效的回避,文晏导演类型叙事的缺点在这部影片被放大了许多。
不管是回忆还是当下,每个场景被带到高潮的方式都低级得趋同。
制造一个惊诧的动作,然后重复。
砸门、撞墙、注射、怒吼、追逐、扔盘子,威亚吊的几次牵拉(同时可怕的逼迫)还一定要撞上生理期的折磨。
类型片的影迷其实不难看清,这些为了无效地传达紧张的动作与语言,只是导演没有尝试寻找更合理的方式。
所以当演员摆出这些姿态——即使完成地出色——看起来都过于滑稽。
更何况她们还要正经地说话与表演,直至场景抵达某种预定的力度。
实在难以抑制说出那个最难绷的段落,她们开始使用逼迫的语气,话语反复拉扯,然后用方言念出最令人震惊的“我杀了人”。
文淇试镜那场戏的笑场,可能是安放这些滑稽的写作的合理选择。
不过还是更难想象在这个安排了各种吸毒、赌博、黑社会运作的议题的影像,如何能使两位00后演员摆出谐谑的姿态。
尚可理解,导演在其他地方制造了错位,把黑社会进入片场的部分写成了黑色幽默的段落。
遗憾的是,两位硬汉与一个怂货的配置,还是呈现为了国产小品喜剧的桥段。
黑社会控制的毒、赌的犯罪系统,这些宏大的罪恶,在现实中是失真的吗?
令人怀疑。
不过影片所呈现的至少是这样——前文所提到的国产喜剧配置,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佐证。
两位女性如何亲历、纠缠并尝试逃离这些危险?
《嘉年华》用两种互不交汇的路径,以受害者与旁观的、以另一种方式亲历的形象,各自敞开视角。
至少两种视角都有一定的说服力,我们能从看到一些东西,将其组合,能将那些罪恶的系统呈现为局部,隐藏着危险的联系。
而《想飞的女孩》舍弃了那些原可以很珍贵的东西,我们不再能看到那些视角的差异性,她们共同面临的危险,都被抽象为空洞的、不可靠的类型元素。
7 ) 请导演把下面这几个未完成填完了再拍吧
1.妹妹的人物性格。
没有一场戏能表现刘浩存的人物性格,告诉观众她都选择合理性。
找了个黄毛、生了个孩子,莫名其妙。
为了挣扎而挣扎。
2.姐妹俩人命运纠葛的必然性。
咋了,表姐妹就必须互相救赎?
别说不是一个妈生的了,就算是亲兄弟姐妹、父母亲子又如何?
人都向阳而生,中国这么大且自由,有什么必然性一定要被一个吸毒的男性长辈困住人生?
断亲是什么很难的事吗?
请导演告诉我不断亲的必然与合理性吧……设置一个表姐妹就以为可以不去做应做之工作,都不如做两个陌生女孩儿之间的故事。
3. 开超市那男孩儿是什么背景和性格?
为什么要帮这姐妹俩?
咋着,来配合拍青春偶像文艺片?
生活不太艰难,做生意是副业?
4. 电影的质感来自一个个戏,每个有效点戏都是无数的细节堆积出来。
但这个是啥?
除了文琪自身的演技在尽力在有限空间里做出人物性格,这里面每个人物刘浩存演的妹妹、姐姐的母亲姑姑、开超市的男主,有一个人物站得住脚吗?
最后结尾,啥也不是
8 ) 观影笔记
#观影笔记#竟然正好过了四个月才看。
二倍速看觉得还可以,不好也不差1.电影的功底、水平在这里的,你要说撇,确实不撇。
细想剧情很狗血,至少拍得不狗血 (置景、年代还原差了些,场景的摆拍感很强。
对比娄烨,娄烨确实凶)2.身为无权的、必将被吸入深渊的年轻女性,那种无望感,是抓到了的。
但人物、剧情、叙事、编排,都经不起细究。
可谓是有形无神无质料剧本和电影化不行。
这种片子即使走形式感(如娄烨),还是要用丰满的现实细节的展现、展演去撑起的。
整个剧情还是有点走过场,两个主角完全是靠本身的魅力和演技、风格 撑起了。
还有那个中老年男演员,也是本身不错。
除此之外,都太走过场了,太像学院派的学生作业 (只是篇幅和气度,多少比学生好些)不得不说刘浩存是天生的演员,老天爷给饭吃。
就是传说中她就站那儿,啥都不干,你观众都在主动帮她演的演员。
当然她演技是不错的。
这样没有任何事情真实发生,全是在表现处境、感受的角色,都完全hold住了。
3.飞这个意向出现很多次,开头的武打替身之飞、乌鸦、乌鸦纹身……意象是好的,用起来总觉得没脱离学院派作业的水平4.文琪的武侠造型真像《刺客聂隐娘》,期待她的古装片。
末尾打打杀杀,飞下楼台,在cue《卧虎藏龙》的玉娇龙吗?
最后跟蝙蝠侠似的飞走飞向观众,技术和呈现上有点搞笑了。
作为一个单独意象,实在跟整体不搭5.片尾多次狗尾续貂了,这片子不仅经不起推敲、也没真的想清楚吧
9 ) 我不懂
很难想象女导加两个新生代这么有灵气的女演员整出来这么一个烂剧本,东一榔头西一锤子。
语言上,一会儿方言一会儿普通话这是要干什么。
角色适配度上,浩存跟女儿像姐妹,女儿存在的意义实在是说服不了观众,文淇戏的情感一下一下的转变得很突兀(不先交代前因后果你放多少遍儿时回忆都没有用😢)。
打着双女主的旗号,加了这样多莫名其妙的男人戏:突兀好心且爱说教的便利店老板、好像在拍杂志大片且担当不合时宜搞笑戏份的反派三人组、贪心的要钱还要爱的反复出现的最后还要靠警察把他抓了才能解决的爹……存也在这部片流了太多看着很好看但是对人设毫无帮助的眼泪,活得一直很痛苦但是自己举报了爹看着他被抓了还要哭的眼泪,突然去看日出然后看着大海哭了的眼泪,还有很多湿漉漉的眼眶,导演是不是太滥用了……无论是剧情安排还是形象构建,都给人一种直来直去硬塞的感觉。
你要讲姐妹情吧,没讲清楚一开始矛盾点是什么;你要讲少女失足吧,后面真的就这样淹死了;你要讲原生家庭吧,姑姑又做错了什么,然后结尾还来回顾幸福开始。
最后搞成了一个禁毒+未成年性安全教育片,很难让人不骂。
最后还是要补充一句,浩存我先不说了,文淇你演坏人戏比演好人戏出彩。
你们不要再装简简单单纯纯爱爱姐妹情,也不要擦一些骗女同进去杀的边,搞女同星恨是你们最后的出路。
(哦,这部片子的恨也没拍出来,以至于什么样的爱都太莫名其妙
10 ) 。
3.10路演场@江南分馆小repo 天呐 这真的很难看 难看到我看完以后都不是很想见到主创的程度。。
主要是剧情出大问题 来回的闪回让回忆也无法连成一个完整的线 都是一个个小点 就好像在解释现在为什么她俩会有这样的情绪 一定要闪回到这个诱因 但是太碎片了 观感上非常的凌乱且无序 妆造我觉得也很奇怪 造型很没有信服力 浩存一直穿的红毛衣倒还好 但她蹦迪时的打扮 文淇去试戏时候的穿搭 都莫名不是很贴她们的角色/人设 身处的状态 以及整个时代背景 很难形容这种感觉 太精致?
太明星感 不够普通人我觉得自己也是有点叛逆情节 我觉得重庆取景绝大多数都有种科幻feel 就是剧情跟着这个环境一样变得特别的魔幻 比如《难哄》《坚如磐石》《少年的你》目前想到这些 可能本身也不是很了解当地风俗所以觉得悬浮 但导演说这几年做过很多田野那我还是相信这个情节和采风比较写实人设 人物塑造上很有问题 我看不出这对姐妹有什么羁绊 不知道为什么就姐妹情深了 特别是在姐姐视角这吸血一家门不是越早逃离越好吗 有一个偏心外甥女的亲妈 这样家庭环境里长大真的会对自己的表妹这么照顾吗 还有很多动作设计卖腐(不知道百合的叫啥 卖姬?
)太明显了 我都有点替她们尴尬 因为完全没必要 女性友谊 姐妹情深 一定要用这么露骨赤裸裸的动作去呈现吗 难道真的不是通过这些贴贴来掩饰其情感上的空白和欠缺吗 剧情也实在是过于狗血了 感觉所有抓马因素都要集齐了 更迷惑的是这两个黑帮反派前期承包的笑点 我前期一直以为这俩来找方笛是真的有啥事 而不是真的来催命的 最后还是真反派 为啥要给他们安插笑点我真的很不解这个点 在娱乐化他们的黑帮行为?
可能我还是太传统不理解为什么要把笑点安插在他们身上 而且那种笑点好无聊啊根本笑不出来 以为串戏到开心麻花了。。
好割裂导演你不是很会意像吗 为什么在这里地飞如此literal。。
而且妹妹说希望露露能像姐姐一样飞她是真的打心底里向往姐姐的生活吗 为了替家里还债做牛做马当一个替身 我真的看着都觉得尬 还有演技方面 我看到夸两位主演演技的人很多 看下来整体是说浩存演的略逊一筹的比较多 我个人觉得那一场浩存说觉得活着跟死了一样从生下来每一件事都是错的 感觉演的很好 那一场印象很深 反而觉得文淇没有接住浩存的戏 但整体这个角色发挥空间也是有限 浩存为什么在戏里瞳仁如此之大 真的有点吓人 戏外看了很多照片视频都觉得很正常啊 想不通 今天的路演给我的感觉也是 快要对路演祛魅了 路演看多了也就这个样 没什么特别的 大部分的回答都没啥新意 但我认为聊创作意图 创作背景 结合参考的影视作品 - 浩存今天有提到导演让她去看一些电影 这些能不能展开说说!
表演背后的故事:文淇说的闷在水里一直在憋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水 我听着都觉得窒息 可以还有浩存海边戏她其实不会游泳这类的 唯一的重庆人演员彭静教她们讲方言 这种女性互助太好了 这些能不能多聊聊!
商业吹捧太多 太有包袱 没什么活人感说实话 而且这种饭圈粉丝向观感不太好 都在吵吵嚷嚷 配角演员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呐喊和关注 整体的谈吐感觉浩存真的是嗲妹妹(非贬义)也有可能声音的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她回答说什么“扶摇直上” 她真的是那种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说的都是无功无过准备好的标准答案的那种乖学生 文淇就更松弛一些 两人的表达都挺好的 风格很不一样 但我最喜欢的竟然是小孩演员 太可爱啦 她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姨母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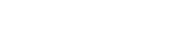


































这剧情跟姜颂一摸一样,到底谁抄袭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