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境》剧情介绍
德国军队就在巴黎城外。格奥尔在最后一刻逃到了马赛。他的行李中带着一个叫Weidel的作家的遗产,这个作害怕遭受迫害而选择了自尽。这些遗产中有一份手稿,一些信件,和墨西哥大使馆对签证的一份担保。只有这些才能证明他们已被允许从这座港口城市离开,离开这里意味着还需要一份来自潜在东道国的入境许可。以Weidel的假身份,格奥尔试图获取船上的一些稀缺通道。难民之间的会谈在他小旅馆的走廊上,领事馆的等候室里,以及港口边上的咖啡厅和酒吧中进行着。格奥尔帮忙照顾着他已逝战友海因茨的儿子,海因茨在逃亡时不幸过世。但他的计划在遇见那个神秘姑娘玛丽时改变了。《过境》基于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撰写的二战同名小说改编,电影以现代马赛为背景,来自过去的人们在这里四处出现。因此,过去的难民会与今日的难民相遇,历史与今生相遇,他们所有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永恒的过境空间。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练爱ING铁道飞虎恋慕猩球崛起知青家庭山田君与7个魔女光影造梦师Ⅱ大奉打更人求婚大作战阿登的狂挫黄大妮侦探语录平凡职业造就世界最强旺扎的雨靴胜利时刻:湖人王朝崛起第二季暂停时光新白发魔女传雪光之灾哆啦A梦:大雄的恐龙铁拳暗黑家族新堂家的复仇城中诡事破产姐妹第二季三坪房间的侵略者埃洛伊塞抗癌的我201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碟仙廉政行动2009舞伎家的料理人
《过境》长篇影评
1 ) 过境
我想困境是本片在极力营造的一个主题,故事发生在纳粹攻陷马赛前,首先就是把这个二战时期的故事放到现代法国街景下的演绎,这是时间上的错乱;空间上他打开了一个以墨西哥大使馆为圆心的难民视角,他们有着不能明文的生活规则,如果无法手握一张离境船票,任何人甚至不能入住旅店,而向秘密警察的告密也成了一种默认,“是羞耻让我们沉默。
”,警察突袭旅店时大家互相凝望。
每个人都在等待着自己的身份被盖章,他们在使馆内热切地倾诉自己的避难故事,游荡在使馆的辐射圈内,又隐匿于各个旅店之中,对彼此冷眼旁观,这样的末世感与阳光充裕的海港城市混乱地重叠在了一起。
但正是这种外部困境下,男主角的视角才显得极为无助与真诚。
故事开始,带着一位已经自杀身亡的诗人的遗物,男主角和负伤的海因茨从已经沦陷的巴黎跳上了去往马赛的火车,在夜晚幽微的蓝色光线里,男主角阅读了诗人遗留的稿件与他妻子的来信,早上醒来时海因茨已经去世了。
从下火车开始,他便是带着两个死亡讯息来到马赛的外来者形象,我想本片最终想讲述的就是这一层身份的困境。
海因茨的妻儿藏在马赛,诗人的妻子一直在寻找丈夫,他鬼使神差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可以选择做海因茨儿子的父亲,也可以是诗人,甚至是诗人妻子的情人医生,但每一次选择便意味着对另一种身份的抛弃,隐藏在身份困惑的背后,就是人与人之间这层情感联结。
“谁会先忘记,离开的人还是被抛弃的人?
”。
葆拉贝尔饰演的妻子在本片再次化身了精灵般的存在,出现在了这个被麻醉的世界。
压抑的社会规则之下,只有她与海因茨的儿子带给了男主角真实的、关于爱的刺痛,他最后给出了那张船票,主动将真实的自己从替身里抽离了出来,我感叹于导演佩措尔德的这分勇气,他将男主角永恒地困在了错乱的时空之中,却带来了一切的可能性,也自然是每个时代的残存的爱与希望。
2 ) [Film Review] Transit (2018) 7.5/10
The final chapter of Christian Petzold’s “Love in Times of Oppressive Systems” trilogy, after BARBARA (2012) and PHOENIX (2014), both scripted by Petzold and the late German filmmaker/critic Harun Farocki (1944-2014), TRANSIT is an adaptation of Anna Seghers’ Nazi-escaping novel and has a daring conceit that challenges the status quo of cinematic transposition.On the face of it, the befogging disjunction between its narrative and temporality (an unspecified contemporary context) persists throughout the whole story, our protagonist is Georg (Rogowski), a young German refugee in France, who flees from Paris to Marseille, assumes the identity of a deceased writer of certain cachet, whose recent suicide hasn’t yet been circulated, to secure a ticket to embark on an ocean-liner, destination Mexico. But in Marseille, he meets the dead writer’s wife Marie (Beer), who relentlessly looks for her husband. Georg falls for her and also manages to get her a ticket without revealing his ulterior scheme, but their quirk of fate is far crueler than the truth itself. Right out the box, audience will be fully aware that the story is not set in WWII but current times, Georg is obviously not running away from Nazis (reckoning that he gets the wind of Germans are coming), and a double take suggests he ought to be an illegal immigrant who tries to lay low and pulls out all stops to leave the Continent. However, curiously and diligently Petzold effaces any trace of modern-day trappings (no cellphone, television, or computer, signs of today’s technology), what we are granted to see in lieu are manuscripts, trains, a flashlight, footballs, a broken radio, nondescript hotel rooms, ocean liners, taxis, embassies, etc., all have been well existed in the WWII period, as if he conspiratorially intimates that what we see is actually what happened during that time, only, in the film, those things are presented in an unmistakable milieu of our reality. Which makes one wonder, is this a new approach of re-imagination? Faithfully complying with the source material’s time-line and story, then put it under the life as we know it without upgrading all its paraphernalia, only subtracting any anachronistic items, therefore, the plot doubly serves as a paralleled allegory, past horror is not so far from being repeated, time and again. Relative to its innovative and sagacious leitmotif, Petzold’s narratological disposition is unfortunately less impressive (abruptly killing off secondary characters for the shocking effect is blasé), dutifully crossing the t’s and dotting the i’s of the monotonous dilemma (a tentative father figure fell by the wayside in a transient sojourn, and an eleventh hour cop-out that becomes a blessing in disguise), although Franz Rogowski comports himself particularly striking with a searing dignity and a tormented reluctance written all over his face, and Paula Beer, often exudes an entrancing restraint and sophistication that is so incongruous with her tender age, comes into her own in the latter stage of the story with a difference, whose seesawing allegiance between three men, her husband, Georg and Richard (Giese), a doctor of her fallback position, keeps us dangling in a heartbeat. Even without a mind-blowing cadenza like he did in PHOENIX, to induce frisson, nonetheless, Petzold infuses TRANSIT with a melodramatic poignancy that stoutly holds its own concomitant with its allegorical connotation and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referential entries: Petzold’s BARBARA (2012, 7.0/10), PHOENIX (2014, 7.8/10).
3 ) Flow of the Void
05/17/2020. Timelessness.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the time. 在时间之外、在虚无里逡巡;也如同行在日光之下尘世之上的无间道。
Almost otherworldly. Strikingly intimate, immersive, and mesmerizing. Spontaneous and grounded in every aspect. Pure embodiment of the characters. His rootlessness and her restlessness. (Does love ground you and bring you back to the “living”? Does it give you a path to take?) Franz自身独特的质地带给了角色微妙的温度、流动性、与隐秘感。
Paula Beer也十分鲜活、复杂、迷人,如活在你漫长的错觉里。
Both of them are beautifully present, true, and nuanced. Loved the breath-giving, open giving-receiving between them. 作者与作品之间的疏离感。
作者性的纯粹,作者却隐而不现。
4 ) 身份的迷失,永远无法抵达的dream land
大概是今年最爱的欧洲电影,它文学性的诗化表达,以及模糊了时间事件空间的艺术手法,都让人深深沉迷。
初看,它有着葡萄牙电影《一千零一夜》的神秘和荒诞色彩,在现代时慵懒的马赛,模糊了时间与空间,上演着二战时种族隔离屠杀前夕的恐怖大逃散。
细看,才发现,所谓历史会重复上演折射当今欧洲难民问题只是它浅显的竞赛片皮囊。
深入去体会,才发现这是一部弃时代不顾只关注人本身作为时代洪流下微不足道个体的电影。
它发出了三段式的诘问: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又将去向何方……剧中每个人都在迷失的身份中,徒劳地寻找着对自身的终极定位。
一趟驶向未知旅途的火车,一艘永远无法抵达dream land 的邮轮,人头攒动的大使馆,人们为一张船票一纸签证奔忙,每个人都在慌张地奔向未知的目的地。
这种个体关于身份的巨大迷失感,是非常令人绝望的,女主角试着用抛弃与被抛弃的关系来找出自己是谁的答案,却依然很枉然,因为最终她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抛弃了自己,她又抛弃了什么,才如此迷失于现在时。
还是这个反复折磨我的问题,在这世间,你我都拥有多重身份,是子女,是父母,是丈夫或妻子,是雇主或雇员……在一轮轮对身份的洗刷中,却遗忘了我是谁,脱离这一切外界赋予的道德和社会的身份,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还真是一时回答不上来啊。
5 ) 过境-影评
故事:一个男人想要凭着假身份过境,最终经过思考成全了另一个男人及女人,反而这俩人因战争波及死亡。
背景将二战德国与犹太人的历史放在了现代;男主和作家一起偷渡,作家却在中途死亡,男主凭借作家的假身份可以过境,中途遇到了作家的妻子和医生,作家妻子在等待丈夫归来,而医生与作家妻子在这个背景下已心生爱慕,男主也爱慕作家妻子,男主想和她一起过境,最终战胜自己的念头,成全他们;没成想反倒害了他们,最终在酒馆了已经出现幻觉了,幻觉中作家妻子来找他,想必真实世界肯定没有生还了;男主已经不在意大清洗了,只是希望她最终会来到这里找她。
看过一些在二战这个德国与犹太人的背景之下的电影,人们做的一些违背道德的事,貌似已经感觉很正常了,男女之间的多角恋,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崩塌,最后再人类本善的觉醒;整个影评演的比较自然,故事不新颖,但是二战背景和现代衔接的很好。
6 ) 窗
德国军队就在巴黎城外。
格奥尔在最后一刻逃到了马赛。
他的行李中带着一个叫Weidel的作家的遗产,这个作害怕遭受迫害而选择了自尽。
这些遗产中有一份手稿,一些信件,和墨西哥大使馆对签证的一份担保。
只有这些才能证明他们已被允许从这座港口城市离开,离开这里意味着还需要一份来自潜在东道国的入境许可。
以Weidel的假身份,格奥尔试图获取船上的一些稀缺通道。
难民之间的会谈在他小旅馆的走廊上,领事馆的等候室里,以及港口边上的咖啡厅和酒吧中进行着。
格奥尔帮忙照顾着他已逝战友海因茨的儿子,海因茨在逃亡时不幸过世。
但他的计划在遇见那个神秘姑娘玛丽时改变了。
《过境》基于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撰写的二战同名小说改编,电影以现代马赛为背景,来自过去的人们在这里四处出现。
因此,过去的难民会与今日的难民相遇,历史与今生相遇,他们所有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永恒的过境空间。
7 ) 无处可去,无家可归
1. 无处可去,无家可归2. 过去的没有过去,新的不新3. 抛弃的,被抛弃的1. 无处可去,无家可归过境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一群逃出纳粹统治德国的人,为了去往美洲,而聚集在马赛等待签证的故事。
签证迟迟不发,在马赛也没有滞留许可,导致这些人就像没有身份的幽灵,游荡在城市中。
他们等待一纸船票,寻找失去的爱人,在看起来没有尽头的等待和寻找中焦灼和消耗,也偶尔相遇,偶尔相爱。
但在那种情况下,注定所有爱都将魂飞魄散。
谁也不知道纳粹会不会永远统治下去,不知道签证到底能不能拿到,不知道清剿部队将在何时到来。
活着的每一刻都在恐惧和焦虑之中,但没有任何能够改变的能力。
他们就像幽灵,不能下沉也不能飞翔,只有悬置,漂浮在异国他乡。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在讲述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故事,还是对我们人生的寓言。
每个人被抛到陌生的世界中,都是不情不愿的,而那个绝对安全的故乡——母亲的子宫,那个混沌、黑暗和未成形的地方,是不可能回去的。
在那里我们没有烦恼,丰腴自足,不会被伤害,没有生存的困境,没有存在的虚无,没有永无止尽的受苦。
可是在我们被扔进世界后,不论在何处,处处是他乡。
所有东西都陌生、未知、带刺,我们不得不在尘世中徘徊,带着挥之不去的背井离乡之异质感,永远在怀念那个回不去的模糊的故乡。
故乡是一种不可追忆的概念,它并不提供一个明确的幻想,也不曾是实际的安身之所,在记忆中没有它的痕迹。
它的存在仿佛是为了证实悲观主义哲学家所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没出生是更好的。
马赛,聚集着一群无处可去,无家可归之人的地方,是人间炼狱的缩影。
马赛并没有收留这些可怜人,只是“好心”地提供一个中转所,让他们的脚能有个站立的地方。
马赛努力尽快赶走这些异乡人,确保它们不会赖在这个地方不走,可对于他们去往美洲,马赛又拒绝提供帮助。
要留在马赛必须提交会离开马赛的证明,可出境签证繁琐又无望,轻易就会陷入循环的漩涡,在不停的申请-等待-过期/否决-申请中耗尽时间和耐心,如果最终是没能离开,结果就只有变成幽灵在异国他乡游荡,或者等来大清扫被扔进集中营变成真正的幽灵。
马赛并不欢迎这些人。
他们的生活卑贱或苟且,丧尽尊严或生不如死,马赛都不关心。
毫无悲悯之心,正如世界对待芸芸众生。
马赛是停留之所,并不是目的地。
而这停留,是充满了小心翼翼、胆战心惊的,怕弄错了什么事情就会被驱逐出去。
在这里的生活是时时刻刻在绝望中煎熬,在等待和寻找中无意义的消耗,而这等待和寻找也不够明确,是一团混沌、模糊、不够干净漂亮的东西。
在两个彼岸之间,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延长的此刻,时间是不走的。
马赛对于这些人就是炼狱,但他们受苦却不是因为过去犯下的罪恶,而是毫无理由的,源自不公正的审判。
他们是因为某种偶然而不得不受罪,却好像他们罪当如此,并毫无同情心地往无辜之人身上倾倒惩戒。
忍受和苟活,是他们能做的唯一的事情。
在一个借来的地方,度过一段借来的时间。
虚妄,荒谬,痛苦,就是全部。
他们等待离开马赛,到一个新地方开启新生活。
但这是不可能的。
片中成功“离开”马赛的人只有几个。
一个是跳楼而死的那位女士,还有女主角和医生,遭遇船难而死。
仿佛在说,对于更美丽的世界的幻想是虚妄的,受苦受难的此处就是世界的全部样子,没有逃离的方法,除非死亡。
死亡是唯一的归处和去处。
可这又算得上什么“离开”呢?
每个人都早晚要死的。
期盼的未来没有到来,所有信仰都沦落为愚弄和欺骗。
像是某个超越的东西,高高在上施舍慈悲说:总要给他们一个念想,让他们能勉勉强强活下去。
片中有一个十分动人的片段。
男主角在修理好非洲男孩的收音机之后,听到故乡童谣的旋律,便跟着低声吟唱了起来。
“大象回家了,鱼回家了,鸟回家了,小鹿回家了”,他们都回家了,你何时回家?
你可有家能回?
永远怀念,永远不能到达。
幸好,人都是要死的。
2. 过去的没有过去,新的不新影片的背景设定在四十年代,却直接采用了当代马赛的街景。
道路上有新型轿车飞驰,警察穿着当代制服,美术馆也和今天的游客能看到的没有区别。
分明讲述的是二战期间的事,建筑和街道却是此时的,扭曲在微妙的悖论中。
导演在采访中直言,拍摄完芭芭拉和不死鸟后,他决心再也不拍年代剧了,因为他觉得那些布景服装道具又费钱又烦人,他再也不想经历了。
就算要拍,也要换一种方式拍,看看能不能在简化这些幕后工作的同时,呈现出历史的情感。
思考之后,他找到了一个超级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直接在二十一世纪的背景下拍二战期间的故事。
省事又省钱,还看起来特别高深,何乐而不为。
(上句是我的主观看法,请忽略。
)过去仍然活在现今之中,就是导演的理念。
过去并不是过去了就没了,它仍然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于某个地方。
过去没有变成古董或木乃伊,它和现今纠缠在一起,仍然影响着,呼吸着。
当我们看见一栋房子,很容易只从此刻看见它,但它不是突然掉到我们眼前的,它是从过去经历无数个现在,才来到现在的。
它在那些亡命之徒苦苦等待的年代就存在,它看见那些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它承载和记录着所有,怎么能因为我们从现在看见它,就否定过去也在其中。
过去蛰居在现今,它一直活着,将一直活下去。
在某些场景,街道和建筑是陈旧且未修缮的,没有多少现代化干净整洁的样子,让观众觉得角色们的确身处上世纪中叶,而在某些场景,那些突然闯进镜头的格格不入的东西,崭新的华丽的建筑,又让观众如梦方醒,对啊,他们是来自过去的幽灵。
过去寓居在此刻,是个很浪漫的想法。
我的脚踩上的每一片土地都浓缩着几万年的历史,我呼吸的空气也有它们自己的经历。
那么当我们去到如今挤满游客的花神咖啡馆,或许仍然能一睹百年前的哲学家们高谈阔论,作家们奋笔疾书,逝去时代的烟雾缭绕以某种方式留存,那种激情,那种不朽的渴望,以及年轻。
那样,它就不仅仅是将怀旧梦想戳成稀巴烂的现代遗物了。
偶尔是浪漫的,经常是残酷的。
即便经过记忆的修饰和美化,过去也不是只有好事发生。
那些刺痛我们的,伤害我们的,留下疤痕的,才是我们记忆更久的东西。
将我们困于记忆的牢笼,在回忆的褶皱中重生,在反复重现中折磨的,可不是什么美好幸福的过往,是悲惨而残忍,永远不能释怀的东西。
赫塔米勒在自传性作品国王鞠躬国王杀人里说:我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总过来叫我忘掉过去。
他们说,你翻来覆去把以前的事说了这么多遍,大家充分知道了你的意思,再说下去,人们要感到厌烦的。
那已经是历史了,是过去的了。
你现在生活在德国不是吗?
罗马尼亚独裁都倒台那么多年了,你为什么还念念不忘呢?
你该写点新的东西,写写关于你现在的东西。
可是,对我来讲,那不是过去的事,那就是现在的事,是现在正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总有乐意当人生导师的人来假意劝慰说,你不要总停留在过去,你要关注当下,你要多看看未来。
此时,怀疑这些人的居心是很有道理的。
他们要么是想充当智者享受一把优越感,要么是在暗示这些东西他们听腻歪了不想再听了,要么是在炫耀生活环境的优越带来的轻飘飘的虚荣。
他们说“忘记过去”的样子,好像人可以在每一时刻重生,以洁白的处子之身面对世界。
过去不会消失,过去一直活着。
它仍然以记忆的形式折磨我,仍然像幽灵缠绕着我的生活,是它塑造了我此时所是的样子。
如果我假装我可以忘得一干二净,欢天喜地地开始新的生活,那就是没有心肝,是对自己的背叛。
要碾碎心头的血肉,把记忆擦得锃亮,要时时咀嚼痛苦,要悔过非我之过,要不停控诉。
当有人要你闭嘴的时候,就更大声地朝他们怒吼。
凭什么不让说?
偏要说,要不停说,要反复说。
受害者如是,加害者更是。
看到过一些人说德国怎么总在拍忏悔历史的东西,一开始觉得很有诚意,是真心悔过,看多了就觉得厌烦,怎么不能拍点新鲜的,揪着以前的东西不放,不也是一种小肚鸡肠?
这大概是因为这些人生活在遥远的东方,无法感同身受,如果改说和邻国的关系,立马就气得跳脚了。
这种可笑的观点我不想多做评论。
就像一个人对奥斯维辛生还者说:这个故事你都说了几千几万遍了,你能不能消停点?
对这种人我们能说什么呢?
在我看来,德国反思历史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还不够多,应当努力创造出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
这件事没有一个合适的停止点,不是再过一百年或二百年,就变成遥远的历史,可以不再说了,要不停说,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德国人活着,就必须不停说,反复说。
电影中另一个悖论的接洽是来自二战期间的德国难民和来自现代社会的北非难民。
他们跨越时空,惺惺相惜,互相帮助,建立纽带,比起男女主之间的爱情动人许多,仿佛影片真正的感情戏是放在这边的,而那边只是功能和隐喻的。
他们一起踢球,一起修收音机,男主轻声唱儿时母亲唱过的摇篮曲,男孩依赖男主,希望他能成为父亲,这一切都那么纯洁和真挚。
可当男主又一次推开大门,看到一群面露惊恐的非洲人时,眼中的错愕也是观众的错愕。
他们的种族、国家、文化、时代都不一样。
唯一联系他们的是相似的处境,是外乡人的身份。
在男主之前或许也有过难民在这片土地,在北非母子之后或许也将有来自不同地方的新的难民。
历史循坏往复,过去了几十年,世界却没有变好。
难民以前有,现在有,以后也会有。
就像历史走过浩浩荡荡几千年,仍然是压迫和暴力的历史,没有什么进步,只是在不同状况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重复上演。
太阳底下无新事。
对于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而言,用的是火枪还是导弹,有什么区别。
对于那些背井离乡的人来说,发生在上世纪还是本世纪,又能带来什么安慰。
虽然不相信人类历史是朝稳定变好的方向发展的,但导演也不站在直接否定历史的立场,认为历史就是bullshit,是权势阶层写的自我吹捧的小说。
没有变好,但可以变化,在不停的反思之中,在艺术作品的教导下,是有变好的可能性的。
虽然只有一点点,而且不怎么乐观,但总比直接封杀可能性要好。
消失的北非母子说不定去了更好的地方,遇难的渡轮上或许有奇迹发生。
奇迹,概率无限收敛于零,不代表等于零。
或许这就是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在虚无主义的海洋上能遥望的微弱的灯塔。
3. 抛弃的,被抛弃的“哪个更难以忘记?
抛弃的,还是被抛弃的?
”这句话第一次由大使对男主说出,第二次由女主对男主说出。
在冒名顶替作家的时候,在陌生国度的街道,那个屡次偶遇的美丽女子,在男主转身的刹那由欣喜转为失落,闷闷不乐地离去,过不久又突然出现,像个徘徊在他身边的鬼魂。
那时候,男主肯定以为这是某种命运,在他和那个女子之间的。
殊不知他以为的命中注定都有迹可循。
并不是什么浪漫的邂逅,只是男女主总是先后脚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打探丈夫下落的妻子说:他才来过,刚走呢。
她就去追,每次追到的都是假的,每次都失望而归。
一直以一板一眼的形象示人的大使突然冒出那样一个伤感的句子,让男主不知如何作答,也搞不明白对方的意图。
他怀疑是在试探身份,恐惧自己说错话而漏了马脚,只好用驴唇不对马嘴的回答含糊过去。
直到后来和女主相识,他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对于这个问题,女主的答案是抛弃的那个更难忘,也即加害者比受害者更难忘,这是女主角对自身立场的设问,也是德国人对自己的回答。
而男主一直没有表达任何观点,因为抛弃和被抛弃对当时的他而言,并不是一个话题。
直到后面他抛弃了女主。
说是男主抛弃了女主,其实有点不公平。
因为在二人想到终于可以逃离这个伤心之地,开心地拥抱、接吻,牵着手,大笑着奔跑时,男主陷入了一厢情愿的幻想。
他以为女主是爱他的,他们此番旅途不仅仅是结伴离开,还包含了之后要一起开始新生活的愿景,比如在墨西哥的某个地方经营一个小修理铺子。
或许在扮演作家的过程中,男主产生了幻觉,以为自己冒领了作家的签证和船票,也可以顶替作家成为女主心里的唯一。
但是,在出租车上,女主那番忘情又有点厚颜无耻的倾诉,让男主恍然大悟,他和医生一样,都只是女主角的中转站,而非她的终点。
所以他中途下车,让医生顶替自己上船。
既是怕在检票过程中被女主识破真相,也是对和女主的关系心灰意冷。
如果是他拿着作家的票上船,他必须向女主解释这一切,必须承担欺骗女主的后果。
但如果让医生拿着作家的票上船,医生是不需要解释任何东西的,他本就一无所知,也不牵涉其中。
因此这也是一种逃避。
或许还有想把所有东西恢复原样的愿望。
是他顶替了作家,才闹出这些事情。
医生和女主原本就是要上船的,但女主听到了丈夫来到马赛的消息,毅然决然下船,医生无奈跟随。
因为自己一时的私欲和侥幸的念头,把两个人的命运搅乱,他必须承担责任。
女主角在上船后见到医生就会明白,丈夫已死,男主一直欺骗了她,她就会断了念想,和医生在一起。
就和几个月前失败的计划一样。
从行为上,是男主抛弃了女主,但从动机上,却更加复杂。
或许可以猜测,在女主抛弃作家的背后,也有许多没被书写的东西。
然而,女主是不可能到达大洋彼岸的。
她的终点是死亡。
曾经,是玛丽抛弃了丈夫,丈夫是离开的(死掉的),玛丽的留下的,她不停地等待和寻找。
现在,是男主抛弃了玛丽,玛丽是离开的,男主是留下的,等待和寻找成了男主的份。
抛弃的成为被抛弃的,留下的成为离开的。
身份的置换,宿命的轮回。
男主一开始扮演作家,此时变成了另一个玛丽。
在结尾,我们知道原来影片是男主在向酒保陈述自己的故事,他用“他”称呼自己。
他曾经出于巧合和私心扮演作家,后来又渴望成为玛丽等待的丈夫,此时他终于成为作家。
在得知翻船事故全员死亡后,男主仍不放弃希望,苦苦等待。
他寄希望于一种叫做奇迹的东西,企盼那千万分之一的概率。
这绝非是他沉浸在幻想中不能自拔,而是因为他需要内心的安慰。
玛丽无疑是死了,观众和男主角都明确地知道。
但如果承认她死透了,男主何以熬过不见天日的日日夜夜。
他已经没有能够离开马赛的希望,等待他的除了蹉跎和消耗,就是死亡。
此时对女主的等待和寻找就成为了他的宗教。
她说不定没有死,她会回来找我。
如果不这么坚信,他如何在这炼狱之中继续活下去?
从此以后,他将在大街小巷追赶每一个相似的身影,将为每一声耳熟的脚步心惊胆战,他将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重来。
往后每一天,他都将如惊弓之鸟,活在捕风捉影之中,不得安宁。
无休止的折磨,无指望的等待。
是他活下去的支撑。
就像女主曾是的那样。
过境像卡萨布兰卡的现代版本。
同样是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两张票,谁去谁留的问题贯穿始终,最终各自得到了解决。
但和卡萨布兰卡的古典情调不同,过境更加现代。
过境的女主角没有那个命中认定之人,没有所谓在你之前之后都是他的那个人。
她不爱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
她看起来深爱作家,但作家在影片开始就下线,也没有进行值得一说的描写。
如果我没有记错,作家没有单人正面镜头。
看完电影我根本不记得作家长什么样子。
这样的刻画当然是有意为之,让作家成为一种概念,一种我们苦苦追寻终而不得的东西的象征。
可我们费劲一生寻找,到头来连自己在找什么也弄不清楚。
有如女主角一次次错认。
她大概早就忘记了丈夫的面容。
永远在等待和寻找,等待的总也不来,寻找的怎么也找不到。
浑浑噩噩,苟且偷生,相爱也只是片刻的幻觉。
迷失,坠落,路径退化为目的本身。
为等待而等待,为寻找而寻找,是绝境中的聊以自慰。
人生几十载,命如草芥,活得艰难,死得轻贱,只有悲凉。
过境是我看过的佩措得作品中最悲观的一部。
其他电影至少保留几分亮色,但本片中连葆拉蓓尔的红裙也死气沉沉。
“先生,您找地狱?
您现在就在这儿啊。
”
8 ) 左岸派的复兴
对于习惯了看电影一定要看一个清楚明白的故事的观众而言,《过境》显然是一部不知所云的电影。
它的故事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甚至于也完全不按照叙事电影的基本逻辑去走。
它忽左忽右,沿着两条叙事路线同时行进,不分主次,令人捉摸不到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主线故事。
但对于《过境》这部电影而言,讲一个什么故事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在哪里讲。
甚至于在哪里讲也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所有的人物都处于同一个时空下,彼此交互、彼此相聚又分离,不追问过往,也没有未来。
从这一点上,《过境》倒可以看做是对阿伦雷乃的一次继承与创新,绝少有人能将这种风格完成得十分精彩。
特别是在影片的最后,男主格奥尔坐在咖啡馆,一直等待着玛丽的归来,此情此景令人惆怅万千,联想起《广岛之恋》结尾处两人在酒吧分别,更添几分致敬的意味。
《过境》中故意的模糊了影片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背景,使得整部电影的发生环境变得无足轻重,以此让我们更能够关注到整个事件发生的空间。
一如《广岛之恋》中模糊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背景,将一个关于相遇、相知、过去、未来的故事演绎得情绪丰沛。
《过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背景,德军兵临巴黎城外,男主格奥尔伪装成另一个人带着一位作家出逃,但却在出境的过程中遇到了阻碍,作家不幸去世。
男主却在出逃过程中,遇到了假身份的真妻子,于是上演了一出爱恨别离。
影片前面的故事线和后面的故事线彼此并没有必要的逻辑关系,甚至于砍掉任意一个故事,另一个依然合理,这就令人怀疑这个故事本身的逻辑问题是否成立。
但诸如阿伦雷乃这样的表现主义导演,则不会这样认为。
他们更倾向于营造出一种时空,来展现这个时空下所有发生的事,即使他们并无明显的逻辑关系,但这个时空依旧是成立的。
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营造出一个“过境”时空,现代的人、过去的人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空里,在这个时空里不断重复过往的爱恨纠缠。
这样的表现方法,更可以看作是对“左岸”派导演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扬。
区别于以巴赞的影响本体论为基础的“新浪潮”电影,这一派导演更着重于电影的文学性,他们经常通过大量场景的对话和哲学思考去完成一个文学性浓厚的主题表达。
但不同于《去年在马德里昂巴德》中人物走走停停,反复叩问记忆存在的必要性,《过境》对伤痕、记忆的呈现更趋向于表现记忆的痛楚与撕心裂肺。
《过境》中的人物呈现出一种对过往的流连忘返,正如影片中反复叩问的“到底是谁先遗忘了谁”一样,导演的心中,搞清这个顺序无比重要。
所有的人物似乎都只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不愿离开,只愿意停留在原地去寻找丢失的过往。
基于故事但不着力于渲染故事,反而去通过故事去发掘潜意识里记忆的要素,正是“左岸”派艺术的表达方式。
他们融合了布莱希特体系、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和潜意识学说。
所以我们在《过境》中看到了布莱希特体系的史诗剧特征,但着力点却不在社会,而在于深刻挖掘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
相比于去解读《过境》的表达主题,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次对“左岸”派导演的回眸一笑。
这也就是为什么看过《广岛之恋》、《去年在马德里昂巴德》多年以后,会觉得《过境》如此的似曾相识但又不尽相同。
《过境》尊重电影的文学性,但又不局限于故事本身,向内开掘出潜意识的天地。
不追求前因、不追究后果,只重当下,只重内在。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目的,也是所有“左岸”派导演的美学诉求。
本文首发于锐影Vanguard,版权属于锐影
9 ) 欧洲难民题材竟能与二战纳粹历史相互穿越互文,这部电影太恐怖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金熊奖呼声最高的影片影片是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的《过境》(Transit)。
被作为柏林电影节“嫡系”部队成员之一的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早在6年前就凭借二战影片《芭芭拉》拿过金熊奖。
今年,剧情讨巧的《过境》却与金熊奖失之交臂,最佳影片奖被罗马尼亚女导演阿迪娜·平蒂列首次执导的长篇《别碰我》摘得。
《过境》的落败可以说“成也历史,败也历史”。
影片《过境》改编自德国著名流亡文学家安娜·西格斯的同名小说。
为了逃避纳粹政权的审判,安娜·西格斯在1933年离开开德国,踏上流亡。
在流亡途中,安娜·西格斯写下了《人头悬赏》、《拯救》、《第七个十字架》等带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小说,这给她带来了世界范围的声誉。
《过境》,是一部散文风味浓厚的作品,刻画了当时流亡者的生活及他们遇到的困难。
可以说,任何一部流亡小说都没有像《过境》那样,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在1940与1941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暂留在法国马赛的那群流亡者的境遇。
安娜·西格斯运用精确的表达和对现实生活艺术化的表现手法,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当时苦等船只的逃亡者的绝望和希望。
已经拍摄过《芭芭拉》和《不死鸟》等二战题材影片的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当然不愿意继续重复自己。
在《过境》中,他向影迷们展示了自己全新的叙事风格。
首先,他把发生在二战时期的故事移植到了当下。
时空的错乱,让人恍惚之间穿越到了过去,当但众多现代化的物品出现时,又会猛的发现所谓的纳粹和二战竟然就发生在现在,只是替换了形式和内容,演变成了欧洲移民问题引发的新纳粹主义。
影片故事只是利用了小说中的人物结构和大致经历,讲述德军逼近巴黎,空袭随时可能毁灭整座城市,而城市内部的大清洗运动此起彼伏。
男主角,德国人格奥尔作为难民之一,从巴黎逃到了港口城市马赛。
他阴差阳错的得到了当时的知名作家威登的亲笔信件和还未出版的小说原稿。
威登独自在旅馆中自杀,尸体被秘密处理,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去世的消息。
于是逃亡到马赛的格奥尔半推半就的“充当”起了威登。
他成功的在大使馆拿到了逃亡的船票,十几天之后,他就可以逃避战火,去到墨西哥,过上平静安逸的生活。
可他与死去同伴儿子的“亲情”牵挂,
与作家威登妻子玛丽的“爱情”纠葛,
让他在“去或留”之间挣扎不已。
二战时期,德军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占领了不可一世的法国,早在占领前几年,德国本土的犹太人或者政治倾向不和的作家和科学家就开始了大逃亡。
作为港口城市的法国马赛就是大批流亡人士的聚集地。
作为其中一员的安娜·西格斯就是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将亲眼所见的纪实改写成了具有艺术手法的小说。
在欧洲难民问题引发的极右组织,新纳粹主义尘嚣而上的当下, 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大胆的将两者搭上了关系。
将二战时期的故事全盘挪移到当下的欧洲背景里,年代错乱感起初让人感觉不适,但随着情节发展却又能从中看出不少对当下世界政治格局以及欧洲社会问题的讽喻,导演这种时空背景错置的实验性手法高明而奏效。
两个时代之间,能指与所指的互换,让主题意义不言而喻:战争和纳粹随时会卷土重来,现代明晃晃的日光下往日的幽魂并未溜走。
《过境》通过男主角格奥尔在马赛短暂的流亡经历,以他的眼展示了新纳粹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和压抑。
所有流亡者都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归属感的缺失导致安全感荡然无存。
格奥尔替代了小说家的身份,可这个对他有利的身份,却煎熬着他的心。
帮死去同胞的孩子修好了收音机,可即将远走他乡格奥尔无法提供长久的陪伴,小孩不愿吃下,最终化掉的巧克力圣代是亲情的瓦解,良心的无奈垮塌。
玛丽一次次的介入格奥尔的生活,一袭红裙、一抹倩影、让格奥尔一丝心动。
可当谜底揭晓,原来玛丽是在寻找丈夫,就是被格奥尔顶替了身份的作家威登时,格奥尔的良心再遭重创。
他先占有玛丽,却因身份的问题备受煎熬,且离去的时间越来越近,这场爱情注定短暂,还未开始,即将结束。
还有那位唠叨不休的逃亡指挥家,那位沉默寡言,带着狗流浪的女人,以及格奥尔失去同胞的哑巴妻子,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奇妙的现代浮世绘。
他们衣冠楚楚,却个个内心凄苦。
那位医生踏上了远去的游轮,却不想最终还是撞到了历史冰山。
看吧,没有人可以逃离,或者,逃离的只是身体,灵魂和心,始终遭受放逐。
《过境》带着历史的遗产,移情今天,让二战的疑云,纳粹的恐怖穿越时空来到了现在。
可怕的是,一切不是电影上的妄语和拟像,他们正真实的发生于现在的欧洲大陆,刺痛着一个又一个不安的心。
《过境》借用了历史,加倍了现代人的焦虑。
影片在时空上的错乱,虽然提高了影片的文本厚度,为主题闭合减少了叙事上的繁琐,但过于松散的结构,以及电影元素之间故意寻求的“断裂”和“距离”,又让普通影迷觉得乏善可陈。
时空错乱带来的新奇感,很快在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纠葛下消耗殆尽,变成弃之可惜的鸡肋,化为一场噱头。
另外,格奥尔在处理小说与电影的文本转译时采用了第三人称旁白的手法。
大段的旁白叙事,揭露了角色的内心,同时负责解读潜文本,有时甚至会推进剧情,这种游离在外的叙事方法,值得商榷。
虽然拉开了观众和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保持中立,以旁观的态度避免共情带来了的理性塌陷,为观众能够更好的思考影片内核提供了空间;但冷冰冰的旁白又稀释了故事的浓度,将戏剧性冲突降到了最低,影响了影片的观感,令人有“出戏”之感。
旁白几乎完全解构了潜文本的存在,让角色失去了需要隐藏起来的内心世界,令对白本来需要提供的求知欲和情感共鸣完全丧失。
这种讲出来的台词,与演员演出来的行为,同时并行的手法,大胆且反叛,虽然新颖,但肯定会引来大批观众的不适,以及传统电影人士的不屑。
《过境》是充满挑战且颇具意义的艺术电影,它邀请观众追随角色一起在原版小说和当代新纳粹主义、反难民情绪上升之间建立联系。
几十年前的社会问题现在仍未过时。
只是如今的我们普遍患上了失忆症,或为自保的选择了缄默不语而已。
但结局必定是,人人都是受害者,就像那场餐厅里的再度重逢,旁白解读围观人充满嫉妒,男女主角深情相拥,可最终还是抵不过命运的作弄,良心的拷问,注定只能分道扬镳,阴阳相隔。
10 ) 时空背景错置的实验手法高明而奏效
以政治挂帅的柏林电影节一直都偏好此类作品,而擅长政治题材的Christian Petzold成为柏林的常客也就不奇怪了。
今年这部入围竞赛单元的新作同样是政治题材,最特别之处在于将二战时期的故事全盘挪移到当下欧洲背景里,年代错乱感起初让人感觉不适,而随着情节发展却又能从中看出不少对当下世界政治格局以及欧洲社会问题的讽喻,导演这种时空背景错置的实验手法相当高明而奏效。
要是按照原著小说来拍摄的话,影片的辨识度和新鲜感就跟其他二战故事没太大区别。
导演在这个时空错置的背景里找到不少跟现实对应的情节,令观众在荒诞幽默的情景里感悟到无比精准的现实意义。
男主角作为德国集中营的逃亡者,在法国港口马赛等待登船的期间接触到不少欧洲难民,讽刺的是这些“难民”都是穿着体面,生活无忧的欧洲白人,他们只为逃避纳粹追捕而流亡。
这无疑让人联想到当下欧洲愈演愈烈的难民问题,两个不同时代的难民各自背负着相异的命运,却殊途同归地将美国当作理想的乐土,影射的意味也随之呼之欲出。
这是否暗示当下欧洲难民问题最终要由美国出手才能得以解决?
相比起这个精心设计而隐喻重重的时空背景,影片里的爱情故事就显得无趣得多。
盗用作家身份的男主角,身世不明的女子,前者对后者的感情像是出于内疚而弥补的赎罪,而后者则始终心系作家丈夫而不惜牺牲感情。
整个爱情线索令影片逐渐陷入俗不可耐的情节剧套路里,连结尾也是一塌糊涂的浪漫感,遗憾地破坏掉之前营造的惊艳时空背景。
倒是这个神秘女子的形象值得思考,她就像一个穿越历史的幽灵在欧洲大陆上游荡,有着耐人寻味的隐喻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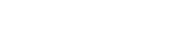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难民题材影片,这些影片里有那么多魔幻狗血故事,我却喜欢这一个。”
新颖结构下的陈词滥调。和这类题材影片比会更好看呢一些,但大段独白是在为叙事减分,虽然它是为完成叙事所服务的。比较聪明的一个作文。但是否有感而发不得而知。#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设定一般,剧情没看点。
三星半。一本能看的小说,时空交错的设置有一种错位的荒诞感,配合大量旁白,倒也算是自成一体。但确实生涩乏味,在飞机上硬着头皮往下看,如果放在平时,估计是没办法看下去的。
一个珍宝似的故事,仿佛出自布鲁诺·舒尔茨之类的小说家之手,简洁但是高度浓缩,回味悠长。男主假扮小说家,在试探他的领事面前说,“小时候去郊游,第二天被老师要求写作文《美好的一天》,就像我的那些同行,从集中营里出来,那些苦难仿佛都是为了写作。但我决定停笔。”真是高级;而且发现导演非常喜欢人死后的幽魂再现,很日常很突然的那一下,让你觉得哪里不对,是不是他(她)死了,然后果然,一场悲剧已经在主人公不在场的时候发生,他看到的只是意念的残影
有想法的嫁接,有设计的表达。
时空错置的设定令人觉得别扭,无法入戏。
感觉叙事有点乱………可能不是我的菜吧
意思是所有评论基本都看过小说,都理解欧洲政治生态,都共情于难民的心理纠葛??!对不起,原谅我的肤浅和无知,我没有办法产生共鸣
过去与当下,观察者美学,历史永恒内在于历史之中。
首先,机翻字幕毁了这片一大半,我居然下不到一个不是机翻的字幕版本。。。其次,这又是一部欧洲白左无病呻吟的装逼片,片子罕见的使用了架空的背景,将二战集中营的犹太人逃难剧情,强行安插到现代莫名其妙的难民身上,我看只有拉尔夫的装逼神片《科里奥兰纳斯》能与之相媲美,借助历史问题把现实政治一通牢骚。最后,这片其实还是个半吊子《艺术人生》的水平,背景空缺、动机飘忽、立场迷离,人家艺术人生好歹还铺垫铺垫才煽情呢,你这大白板的陌生上来情感纠葛给谁看啊?现代人很忙的,认识你是个谁谁谁?大概只有白左文艺青年喜欢吧。PS,用旁白推动剧情和内心的电影,注定是垃圾
将小说文字以随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布景甚至不加一丝修饰,现代马赛和二战时期似乎也没有太多不同,将难民危机隐喻在二战欧洲逃亡之中,机智又精巧,但是无关紧要的人物太多,有些莫名。男主怕是有一个月没睡觉了吧,那黑眼圈…
把一个二战故事放置到当下拍摄环境中,比如角色逃离纳粹追捕的时候可能会路过耐克商店,由此提炼出欧洲难民问题,而这又包裹在一个寻找身份和爱情的悬疑故事之下。佩措尔德精准的叙事技巧如同大海捞针在这违和奇情狗血的设定和故事中找到了那微妙的平衡,看起来竟然如此自然流畅天衣无缝舒服极了。
20240910重看,观感四星不变//确实遵循了文学化的叙事和独白,比《芭芭拉》更具有象征的意味,时空交替下的爱恨与迷朦让我清楚,佩措尔德将会永远有能力捶打我心。
3.5,稍弱于《不死鸟》,但技法上还是非常精致。
典型无空间叙事
#siff21# 蓝天下的马赛,没有难民的一席之地;驶向希望的大船,躲不过命运的捉弄。格调优雅的旁白下其实是个极度浪漫的爱情故事,现代化的二战环境,在绝望的同时又多了一份明亮,就像片尾最后的回眸。
看了55分钟都不知道演了些什么,叠加行情不好,真是糟心。
太糟糕了,乏味得可怕,前两次尝试都看了个开头就看不下去了,第三次下定决心看了一半多,实在忍不住关了。一点儿二战的紧张感都没有,演员都是来春游的吗?
战争随时会卷土重来,现代明晃晃的日光下往日的幽魂并未溜走。不会说话的女人就像缄默的历史,遗忘过去的女人就像失忆的今天。我们带着历史的遗产,移情今天。帮孩子修好咿咿呀呀的收音机,只留下化掉的巧克力圣代。那一袭红裙、一抹倩影、一丝心动,混着逃难的惶恐,成为伤痕的守门员,撞到历史冰山。